時(shí)間:2022-07-23 09:00:10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chuàng)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繼承法意見,希望這些內(nèi)容能成為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jìn)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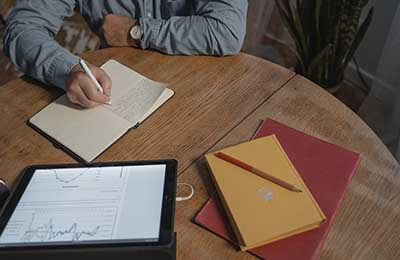
【關(guān)鍵詞】放棄繼承;權(quán)利性質(zhì);撤銷權(quán)
一、放棄繼承本身的權(quán)利性質(zhì)
首先,要明確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時(shí)間,應(yīng)當(dāng)在繼承開始后至遺產(chǎn)分割前。我國(guó)《繼承法》第二十五條規(guī)定“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應(yīng)當(dāng)在遺產(chǎn)處理前,作出放棄繼承的表示。沒有表示的,視為接受繼承。”繼承開始之前,不存在放棄繼承的問題。因?yàn)椋@時(shí)繼承人只是具有一種期待權(quán),即將來繼承遺產(chǎn)的可能性。因此,假如某繼承人在被繼承人死亡之前曾向其他法定繼承人作出過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但在被繼承人死亡之后沒有重申這種意思表示,應(yīng)當(dāng)視為接受繼承。
其次,放棄繼承指的就是放棄繼承權(quán),關(guān)于它的權(quán)利性質(zhì)的認(rèn)定必然涉及到繼承權(quán)的權(quán)利性質(zhì)。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在行使放棄繼承的權(quán)利時(shí),繼承權(quán)同繼承人的主觀意志相聯(lián)系,是具有現(xiàn)實(shí)性、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繼承權(quán),符合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一般理論;另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承認(rèn)繼承權(quán)是基于身份而產(chǎn)生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應(yīng)著重強(qiáng)調(diào)它的專屬性,放棄繼承的行為雖然也是以財(cái)產(chǎn)為標(biāo)的的,但畢竟與買賣、贈(zèng)與等行為不同,具有一定的身份性質(zhì)。因此,前者認(rèn)為放棄繼承可以成為債權(quán)人撤銷權(quán)的標(biāo)的,后者持相反觀點(diǎn)。
然后,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從放棄繼承制度設(shè)立的宗旨上看,我國(guó)《繼承法》采取的是當(dāng)然繼承主義,遺產(chǎn)的繼承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規(guī)定,至于繼承人的意思如何,則在所不問。而放棄繼承制度的設(shè)立,正是為了使繼承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自由意思決定是否溯及地不取得被繼承人的遺產(chǎn)。這是社會(huì)進(jìn)步的法律表現(xiàn),更是一種人格自由的體現(xiàn)。由此可知,放棄繼承制度本身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功能,即使其在行使之際,使繼承人的債權(quán)人受有某些不利益,也不能因此而成為債權(quán)人撤銷權(quán)的標(biāo)的。,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放棄繼承的自由必須得到限制,不能損害國(guó)家、社會(huì)和第三人的利益,否則容易造成權(quán)力濫用。
筆者認(rèn)為:既然現(xiàn)代民法中的繼承指的是財(cái)產(chǎn)繼承,繼承人取得被繼承人的財(cái)產(chǎn)是繼承權(quán)的核心內(nèi)容,承認(rèn)繼承權(quán)是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權(quán),那么繼承權(quán)就應(yīng)該符合一般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特征。在物權(quán)法已經(jīng)實(shí)施的情況下,所謂放棄繼承權(quán),是否就是放棄本可繼承的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關(guān)于這個(gè)疑問,應(yīng)當(dāng)從兩種情況考慮:
1、繼承人不放棄繼承時(shí),則從繼承開始時(shí)取得遺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所有繼承人共有),適用的法律依據(jù)是:(1)《物權(quán)法》第二十九條:因繼承或者受遺贈(zèng)取得物權(quán)的,自繼承或者受遺贈(zèng)開始時(shí)發(fā)生效力。(2)《繼承法》第二條 :繼承從被繼承人死亡時(shí)開始。
2、如果繼承人放棄繼承,放棄的就不僅僅是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而是繼承權(quán),即既得的繼承權(quán),繼承權(quán)不等于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法律依據(jù)是:(1)《繼承法》第二十五條: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應(yīng)當(dāng)在遺產(chǎn)處理前,作出放棄繼承的表示。沒有表示的,視為接受繼承。(2)《繼承法意見》第49條規(guī)定:“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應(yīng)當(dāng)在繼承開始后、遺產(chǎn)分割前作出。遺產(chǎn)分割后表示放棄的不再是繼承權(quán),而是所有權(quán)”。(3)《繼承法意見》第51條規(guī)定:“放棄繼承的效力,追溯到繼承開始的時(shí)間”。如果放棄了,那放棄的意思表示是可以回溯的,也就是在繼承發(fā)生的時(shí)候就已經(jīng)放棄了。
因此,在不存在放棄繼承的情況下,按照物權(quán)法第29條規(guī)定時(shí)點(diǎn)取得物權(quán)。否則,不能適用物權(quán)法的規(guī)定,因?yàn)椤独^承法》(包括《繼承法意見》)應(yīng)當(dāng)優(yōu)先適用。
二、債權(quán)人撤銷權(quán)的標(biāo)的是否包放棄繼承
債權(quán)人撤銷權(quán)起源于羅馬法,因它是由羅馬法務(wù)官保羅(Paulus)所創(chuàng)設(shè)的概念,故又稱為保羅訴權(quán)i。查士丁尼《法學(xué)總論(法學(xué)階梯)》有明文規(guī)定(Inst.,4.6.6.) ii。它是指?jìng)鶛?quán)人在其債務(wù)人實(shí)施減少其財(cái)產(chǎn)的法律行為害及債權(quán)時(shí),得請(qǐng)求法院予以撤銷的權(quán)利。當(dāng)債務(wù)人與第三人實(shí)施法律行為,使其作為債權(quán)擔(dān)保的責(zé)任財(cái)產(chǎn)不當(dāng)減少,債權(quán)人可以請(qǐng)求法院撤銷債務(wù)人與第三人的法律行為,害及債權(quán)人利益時(shí),恢復(fù)債務(wù)人的財(cái)產(chǎn),保障債權(quán)的實(shí)現(xiàn)。
債權(quán)人撤銷權(quán)的成立要件,包括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
1、客觀要件分為四點(diǎn):(1)債務(wù)人實(shí)施了處分財(cái)產(chǎn)的行為。(2)債權(quán)人對(duì)債務(wù)人須存在有效的債權(quán)。(3)債務(wù)人的行為須有害于債權(quán)人的債權(quán)。(4)債務(wù)人的行為必須以財(cái)產(chǎn)為標(biāo)的。
2、主觀要件: 現(xiàn)代民法在撤銷權(quán)要件構(gòu)成方面的理論是有償行為以主觀惡意為撤銷權(quán)成立要件;無償行為則僅須滿足客觀要件即可成立撤銷權(quán)。
現(xiàn)在探討下放棄繼承時(shí)債權(quán)人的撤銷權(quán)的行使是否符合構(gòu)成要件。
第一,對(duì)于合同法第74條規(guī)定,放棄繼承是不是無償轉(zhuǎn)讓財(cái)產(chǎn)?肯定說認(rèn)為因?yàn)槔^承一開始,就承受了被繼承人財(cái)產(chǎn)上的一切權(quán)利義務(wù),因此放棄繼承的單獨(dú)行為就是無償處分行為,所以債權(quán)人可以行使撤銷權(quán)。按照《繼承法意見》第46條規(guī)定,法院判決確定的債務(wù)或者其他法定債務(wù)應(yīng)該是債務(wù)人的法定義務(wù)(擴(kuò)張解釋)。“繼承人因放棄繼承權(quán),致其不能履行法定義務(wù)的,放棄繼承權(quán)的行為無效。”――《繼承法意見》第46條。筆者認(rèn)為,從誠(chéng)信和習(xí)慣來講這里的“法定義務(wù)”應(yīng)給是包括“欠債還錢”,至少是通過法院判決確定的債務(wù),所以作擴(kuò)張解釋。
第二,《繼承法意見》第49條規(guī)定:“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應(yīng)當(dāng)在繼承開始后、遺產(chǎn)分割前作出。遺產(chǎn)分割后表示放棄的不再是繼承權(quán),而是所有權(quán)”和第51條規(guī)定:“放棄繼承的效力,追溯到繼承開始的時(shí)間”。這兩個(gè)規(guī)定能不能說明在繼承開始后遺產(chǎn)分割前,繼承人只是享有繼承權(quán)而不享有所有權(quán)呢?應(yīng)該可以肯定繼承人放棄的是繼承權(quán)不是所有權(quán)。那么,繼承權(quán)具有人身專屬性,即使其具有財(cái)產(chǎn)屬性,拋棄它對(duì)債權(quán)人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債權(quán)人也不能撤銷。
第三,如果第二點(diǎn)成立,《繼承法意見》第46條和第49條也不會(huì)發(fā)生沖突。也就是說,放棄繼承不等于合同法第74條意義上的無償轉(zhuǎn)讓財(cái)產(chǎn)行為。從人權(quán)保護(hù)的角度,筆者贊成第二點(diǎn),承認(rèn)放棄繼承不屬于無償轉(zhuǎn)讓財(cái)產(chǎn)行為。
第四,從撤銷權(quán)行使的目的上來說,它的目的在于恢復(fù)債務(wù)人的責(zé)任財(cái)產(chǎn),而不在于增加債務(wù)人的責(zé)任財(cái)產(chǎn),故債務(wù)人拒絕受領(lǐng)某種利益(比如拒絕接受贈(zèng)與、拒絕第三人承擔(dān)債務(wù)等)時(shí),債權(quán)人不得提出撤銷,否則侵害了債務(wù)人行使權(quán)利的自由。
第五,雖然繼承權(quán)是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權(quán),但是包含一定的人身屬性。繼承所取得的財(cái)產(chǎn)更具有人身性質(zhì),該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取得必須由具有人身屬性的人員決定、行使,他人不能取代iii。而繼承權(quán)的放棄是繼承人的決定的一種,應(yīng)當(dāng)屬于身份行為。
因此,放棄繼承不是無償轉(zhuǎn)讓財(cái)產(chǎn)的行為,應(yīng)當(dāng)屬于身份行為,不符合債權(quán)人行使撤銷權(quán)的構(gòu)成要件,不問動(dòng)機(jī)如何,放棄繼承是個(gè)人行使權(quán)利的自由,第三人不得請(qǐng)求撤銷。
結(jié) 論
綜合兩個(gè)問題的分析,可以得出結(jié)論:“債務(wù)人放棄繼承權(quán),債權(quán)人可否行使撤銷權(quán)”這個(gè)問題的實(shí)質(zhì)是人格自由與交易安全的沖突。在兩種權(quán)利發(fā)生沖突時(shí),就應(yīng)權(quán)衡兩種制度的目的和功能,決定應(yīng)優(yōu)先保護(hù)哪一種權(quán)利。隨著我國(guó)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交易安全顯得尤為重要,《合同法》中的債的保全制度的相關(guān)規(guī)定正是其重要性的體現(xiàn)iv。在我國(guó)民法理論中,無論是接受還是放棄繼承,都是一種人格自由的表現(xiàn)。
但是,在提倡“以人為本”的現(xiàn)代中國(guó),從價(jià)值衡量上來看,人格自由應(yīng)較債的保全處于優(yōu)越地位,應(yīng)優(yōu)先尊重放棄繼承中所體現(xiàn)的債務(wù)人的人身自由。
那種認(rèn)為“債權(quán)人同債務(wù)人進(jìn)行交易時(shí),不僅會(huì)考慮債務(wù)人當(dāng)時(shí)的信用狀態(tài),而且對(duì)于債務(wù)人將來可能因繼承而獲得的財(cái)產(chǎn)狀況也會(huì)予以考慮的”的觀點(diǎn),簡(jiǎn)直就是“異想天開”!難道債權(quán)人在交易時(shí)需要把債務(wù)人的家庭情況都調(diào)查清楚?放棄繼承與誠(chéng)信原則或者說權(quán)利濫用沒有必然聯(lián)系,而是人格自由的體現(xiàn)!
注釋:
i[英]巴里?尼古拉斯.羅馬法概論[M].黃風(fēng)譯.法律出版社,2000.
ii[羅馬]查士丁尼:.法學(xué)總論――法學(xué)階梯[M].張企泰譯.商務(wù)印書館,1989:207.
栗辛與栗林、栗浩、栗麗均為被繼承人栗某的子女。栗某生前立有一份代書遺囑,該遺囑系栗某的孫女即栗辛之女栗之代書,有栗某本人的簽名。該代書遺囑的內(nèi)容是將栗某生前所有的房屋由栗辛繼承。遺囑之后附有兩位見證人對(duì)此遺囑的見證書和栗某對(duì)涉案房屋在其去世后由栗辛繼承的談話記錄,談話記錄也是由栗某的孫女栗之代書,有栗某本人簽名。
在栗某去世后,栗辛以該代書遺囑所載內(nèi)容為由,主張繼承案涉房屋,而栗林、栗浩、栗麗認(rèn)為該代書遺囑不符合法定要求,主張遺囑無效,按照法定繼承方式繼承賈某遺產(chǎn)。
來一點(diǎn)家法:
由孫女作為代書人或者見證人的代書遺囑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律師分析:
依照《繼承法》的基本理論,按照遺囑書寫主體是否為遺囑人本人,遺囑可以分為自書遺囑和代書遺囑兩類。自書遺囑是指遺囑人親筆書寫并簽名和注明時(shí)間的遺囑。代書遺囑是由兩個(gè)以上見證人在場(chǎng)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日期,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的遺囑。《繼承法》第十七條第三款明確規(guī)定:“代書遺囑應(yīng)當(dāng)有兩個(gè)以上見證人在場(chǎng)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第十八條規(guī)定:“下列人員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三)與繼承人、受遺贈(zèng)人有利害關(guān)系的人。”據(jù)此可知,案涉代書遺囑的代書人栗之系栗辛之女,與其有直接利害關(guān)系,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案涉見證雖表明該遺囑書有兩位見證人但他們均沒有代書,因此案涉代書遺囑并不符合代書遺囑的上述形式要件。
遺囑的形式,就是遺囑人處分自己財(cái)產(chǎn)的意思的表示方式。立遺囑是要式民事法律行為,遺囑形式必須符合法律規(guī)定,才能產(chǎn)生法律效力。我國(guó)現(xiàn)行遺囑形式及其效力規(guī)則主要規(guī)定在《繼承法》和《繼承法意見》中。《繼承法》對(duì)于遺囑的形式予以明確規(guī)定的立法本意在于充分保證遺囑真實(shí),以維護(hù)遺囑自由原則。
具體而言,遺囑形式遵循嚴(yán)格法定主義的法理依據(jù)在于:一方面,遺囑畢竟是立遺囑人對(duì)其財(cái)產(chǎn)的終意處分,且在其死后才能得以執(zhí)行,因此,為了確保其真實(shí)性和嚴(yán)肅性,法律必要對(duì)遺囑設(shè)以嚴(yán)格的要式性要求,來最大限度地防止他人偽造、篡改遺囑內(nèi)容。比如,自書遺囑的內(nèi)容須為被繼承人親筆書寫,這樣就比較容易識(shí)別遺囑書寫的主體,偽造自書遺囑的難度就比較大。并且,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自己書寫,更能體現(xiàn)遺囑人的真實(shí)意思。代書遺囑是由他人書寫,立遺囑人雖有簽名,但其意思表示要通過他人的代書來表達(dá),其表達(dá)個(gè)人意愿的自由度會(huì)有所降低,如果沒有其他形式要件的約束,立遺囑人在他人脅迫或誘導(dǎo)下簽名或者他人偽造遺囑的情形就容易發(fā)生。另一方面,《繼承法》對(duì)于代書遺囑的形式要求雖然嚴(yán)格,但是并非苛刻,并不需要立遺囑人付出太大代價(jià)即可以實(shí)現(xiàn)。即立遺囑人意圖通過代書遺囑的形式來處分其身后的財(cái)產(chǎn),只須找到兩個(gè)以上的無利害關(guān)系的人來見證并由其中一人代書即可。如果這一相對(duì)簡(jiǎn)單的形式要求都無法滿足,該代書遺囑是否能夠反映立遺囑人的真實(shí)意圖就值得懷疑,遺囑的真實(shí)性和客觀性就不易得到保證,遺囑自由原則也就會(huì)落空。因此,有必要對(duì)《繼承法》關(guān)于代書遺囑法定形式要件的要求予以從嚴(yán)掌握,對(duì)違反法定形式要件的代書遺囑,不宜認(rèn)定為有效。
綜上所述,本案中賈辛的訴訟請(qǐng)求不能得到法院支持,賈某的遺產(chǎn)將按照法定繼承的方式進(jìn)行繼承。
遺囑繼承作為當(dāng)代當(dāng)事人之間一種重要的繼承方式之一,因此,如何運(yùn)用正確的法律途徑來保護(hù)當(dāng)事人的合法權(quán)利,則成了遺囑繼承中的首要問題,本文圍繞遺囑繼承的含義、遺囑所采用的方式、遺囑公證需要提交的證明材料、遺囑與遺贈(zèng),法定繼承之間的異同、遺囑繼承制度等幾個(gè)方面作探討:
【 關(guān)鍵詞 】遺囑繼承 繼承法 繼承權(quán)公證 法定繼承 遺贈(zèng)
【Content summary 】
Inherit one of the ways as a kind of important one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parties in testate succession, so, how to use the correct legal way to protect the party's lawful right, have become primary problem in testate succession, this text notarizes the identification material , testament that needs submitting and bequeathes around the testate succession meaning , testament way , testament adopted, such several respects a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during intestate succession , testate succession system ,etc. are probed into :
【 Keyword 】Testate succession Inheritance law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is notarized Intestate succession Bequest
一、遺囑繼承概述
(一)遺囑繼承的概念及特征
遺囑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遺囑包括死者生前對(duì)其死后一切事物作出處置和安排的行為,《繼承法》上的遺囑采用狹義說,所謂遺囑繼承是指法定繼承的對(duì)稱,是指遺囑中所指定的繼承人根據(jù)遺囑中對(duì)其所應(yīng)當(dāng)繼承的遺產(chǎn)種類、 數(shù)額等規(guī)定,繼承被繼承人遺產(chǎn)的一種繼承方式。立遺囑的人叫遺囑人,根據(jù)遺囑規(guī)定有權(quán)繼承被繼承人遺產(chǎn)的法定繼承人叫遺囑繼承人。立有遺囑的, 按遺囑繼承的方式處理遺產(chǎn),遺囑所涉及的遺產(chǎn)不再按法定繼承的方式處理。 在遺囑繼承中,遺囑繼承人所繼承的遺產(chǎn)應(yīng)當(dāng)是遺囑中所指定應(yīng)由其繼承的遺產(chǎn),在種類、數(shù)額上都應(yīng)與遺囑的指定相符。遺囑繼承人在按照遺囑繼承后, 不影響其作為法定繼承人繼承其應(yīng)得的法定繼承份額。因此,遺囑繼承也稱“指定繼承”。遺囑繼承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遺囑繼承是單方法律行為。公民設(shè)立遺囑不需要征得繼承人或其它組織和個(gè)人的意見,只要本人通過一定的形式作出意思表示,就發(fā)生法律效力。遺囑人根據(jù)自己的意愿,還可以變更或撤消所立的遺囑,無須他人商議。
(2)遺囑是遺囑人死后生效的法律行為。遺囑是遺囑人生前所為的法律行為,然而這種法律行為在生前只是對(duì)個(gè)人財(cái)產(chǎn)進(jìn)行了預(yù)先處分,它的法律效力應(yīng)當(dāng)從遺囑人死亡開始。
(3)遺囑人必須具有遺囑能力。只有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人,才有遺囑能力,凡是沒有行為能力的所立的遺囑均不能發(fā)生法律效力。[1]
(二)、遺囑采用的方式
根據(jù)我國(guó)有關(guān)法律,遺囑可采用如下幾種方式:
(1)公證遺囑。公證遺囑即遺囑人經(jīng)公證機(jī)關(guān)辦理的遺囑。公證遺囑的方式是最嚴(yán)格的遺囑方式,能確實(shí)保障遺囑人的意思表示的真實(shí)性,公證遺囑也是處理遺囑繼承糾紛最可靠的證據(jù)。
(2)自書遺囑。遺囑人自己書寫的遺囑,稱為自書遺囑。為遺囑人親筆將自己的意思用文字表達(dá)出來。
(3)代書遺囑。代書遺囑是由他人書寫的遺贈(zèng)。代書遺囑通常是在遺囑人不會(huì)寫字或因病不能寫字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但為了保證人書寫的遺囑確實(shí)是遺囑人的真實(shí)意思,減少糾紛, 應(yīng)由二人以上的見證人在場(chǎng)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書人、其他在場(chǎng)見證人和遺囑人在代書遺囑上簽名。
(4)錄音遺囑,錄音遺囑是由錄音機(jī)錄制下來的遺囑人口授的遺囑。用錄音遺囑容易被偽造和剪輯,因此,法律規(guī)定以錄音形式立的遺囑,應(yīng)當(dāng)有兩個(gè)以上見證人在場(chǎng)見證,以證明遺囑的真實(shí)性。
(5)口頭遺囑。口頭遺囑是由遺囑人口頭表達(dá)并不以任何方式記載的遺囑。口頭遺囑完全靠見證人表述證明,極其容易發(fā)生糾紛。因此法律規(guī)定遺囑人只能在危急的情況下才可以立口頭遺囑, 并且必須有二個(gè)以上見證人在場(chǎng)見證。危急情況解除后,遺囑人能夠用書面或錄音形式立遺囑的,應(yīng)當(dāng)用書面形式或錄音形式立遺囑,所立口頭遺囑無效。
(三)、遺囑繼承權(quán)公證需提交的證明和材料
繼承權(quán)公證是指公證機(jī)關(guān)依照法律、法規(guī)、政策,為保護(hù)公民個(gè)人財(cái)產(chǎn)的合法權(quán)利,根據(jù)當(dāng)事人的申請(qǐng)辦理確認(rèn)繼承權(quán)的公證。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提供下列證明、材料:
1)當(dāng)事人的身份證明復(fù)印件;
2)當(dāng)事人填寫的繼承權(quán)公證申請(qǐng)表;
3)被繼承人遺產(chǎn)的產(chǎn)權(quán)證明;
4)法定繼承人放棄繼承權(quán)的需提交聲明書;
5)被繼承人的死亡證明及其他法定繼承人的死亡證明;
6)被繼承人的婚姻、父母、子女情況證明及有關(guān)親屬關(guān)系證明;
7)被繼承人的遺囑書;
8)遺囑執(zhí)行人的身份證明及復(fù)印件;
9)其他需要提供的證明、材料。
(四)、遺囑的法定要件
遺囑的法定要件分為形式要件和實(shí)質(zhì)要件: 遺囑的形式要件是指遺囑的制作、設(shè)立的法定方式。根據(jù)繼承法第17條規(guī)定:遺囑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即公證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口頭遺囑。遺囑的實(shí)質(zhì)要件,指法律對(duì)所立遺囑內(nèi)容的要求:(1)遺囑人在立遺囑時(shí)必須具有行為能力。(2)遺囑必須是遺囑人的真實(shí)意思,脅迫、欺騙所立的遺囑及偽造的遺囑均無效。(3)遺囑不得取消缺乏勞動(dòng)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要為他們保留必要的遺產(chǎn)份額。(4)遺囑只能處分被繼承人個(gè)人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于有效遺囑的實(shí)質(zhì)要件,繼承法第16、19、22條分別作了規(guī)定.下面舉個(gè)案例來說明:
案情:我的兩個(gè)兒子都在外地工作,平日多虧鄰居張三毛的照顧。前不久,我寫下遺囑,言明我死后存款3萬元和一棟木屋歸張三毛所有,并經(jīng)村干部作了證明。有人說兩個(gè)兒子是我遺產(chǎn)的法定繼承人,我的遺囑剝奪了他倆的繼承權(quán),因而是無效的。請(qǐng)問:這份遺囑有效嗎?
評(píng)解:這份遺囑無論實(shí)質(zhì)要件還是形式要件,都沒有違背法律的規(guī)定。根據(jù)我國(guó)現(xiàn)行繼承法第5條規(guī)定:繼承開始后,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有遺囑的,按遺囑繼承或者遺贈(zèng)辦理;有遺贈(zèng)撫養(yǎng)協(xié)議的,按照協(xié)議辦理”可見,遺囑繼承的效力高于法定繼承時(shí),你的兩個(gè)兒子不能以他們是法定繼承人為由駁斥張三毛.
(五)、遺囑繼承權(quán)的喪失
繼承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喪失繼承權(quán):
(1)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無論是既遂還是未遂,均應(yīng)確認(rèn)其喪失繼承權(quán)。
(2)未爭(zhēng)奪遺產(chǎn)而殺害其他繼承人的;繼承人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無論是既遂還是未遂,均應(yīng)確認(rèn)其喪失繼承權(quán)。
(3)遺棄被繼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繼承人情節(jié)嚴(yán)重的;繼承人虐待被繼承人情節(jié)是否嚴(yán)重,可以從實(shí)施虐待行為的時(shí)間、手段、后果和社會(huì)影響等方面認(rèn)定。
虐待被繼承人情節(jié)嚴(yán)重的,不論是否追究刑事責(zé)任,均可確認(rèn)其喪失繼承權(quán)。
(4)偽造、篡改或者銷毀遺囑,情節(jié)嚴(yán)重的。
繼承人虐待被繼承人情節(jié)嚴(yán)重的,或者遺棄被繼承人的,如以后確有悔改表現(xiàn),而且被虐待人、被遺棄人生前又表示寬恕,可不確認(rèn)其喪失繼承權(quán)。繼承人偽造、篡改或者銷毀遺囑,侵害了缺乏勞動(dòng)能力又無生活來源的繼承人的利益,并造成其生活困難的,應(yīng)認(rèn)定其行為情節(jié)嚴(yán)重。[2]
二、遺囑繼承與相關(guān)概念的關(guān)系
(一)遺囑繼承與遺贈(zèng)
遺贈(zèng)是公民以遺囑方式將個(gè)人財(cái)產(chǎn)贈(zèng)給國(guó)家、集體或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而于其死亡時(shí)發(fā)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為。立遺囑的公民為遺贈(zèng)人,接受遺贈(zèng)的人為受遺贈(zèng)人。遺贈(zèng)與遺囑繼承都是通過遺贈(zèng)方式處分,這兩種方式在形式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區(qū)別是明顯的,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繼承法的規(guī)定,遺囑繼承與遺贈(zèng)的主要區(qū)別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幾方面:(一)遺囑繼承人與受遺贈(zèng)人的范圍不同。遺囑繼承人只能是法定繼承人范圍以內(nèi)的人,而受遺贈(zèng)人可以是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公民,也可以是國(guó)家或集體單位。(二)遺囑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后遺產(chǎn)分割前未明確表示放棄的,即視為繼承。而受遺贈(zèng)人在知道或應(yīng)當(dāng)知道受遺贈(zèng)后兩個(gè)月內(nèi)未作出接受遺贈(zèng)表示的,視為放棄,即喪失受遺贈(zèng)權(quán)。
當(dāng)遺囑繼承或遺贈(zèng)附有一無,遺囑繼承人或受遺贈(zèng)人無正當(dāng)理由不履行義務(wù)的,所作出的處理;《繼承法執(zhí)行意見》第四十三條規(guī)定:“附義務(wù)的遺囑繼承或遺贈(zèng),如義務(wù)能夠履行,而繼承人、受遺贈(zèng)人無正當(dāng)理由不履行,經(jīng)受益人或其他繼承人請(qǐng)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義務(wù)那部分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由提出請(qǐng)求的繼承人或受益人負(fù)責(zé)按遺囑人的意愿履行義務(wù),接受遺產(chǎn)。”
也就是說,對(duì)于不履行遺囑義務(wù)的遺囑繼承人或受遺贈(zèng)人,有關(guān)單位和個(gè)人可以請(qǐng)求人民法院取消其接受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并且愿意履行義務(wù)的,可接受遺產(chǎn)。其中的“有關(guān)單位”是指被繼承人的工作單位,遺囑繼承人或受遺贈(zèng)人的單位和國(guó)家有關(guān)機(jī)關(guān)、社會(huì)團(tuán)體等;“個(gè)人”包括被繼承人的親屬、遺產(chǎn)執(zhí)行人、遺產(chǎn)管理人、法定繼承人、遺囑繼承人、受遺贈(zèng)人、履行義務(wù)的受益人,以及其他利害關(guān)系人。應(yīng)注意,按法律規(guī)定,除由人民法院經(jīng)過法定的程序以外,任何組織、單位及個(gè)人無權(quán)隨意取消遺囑繼承人或受遺贈(zèng)人接受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
(二)遺囑繼承與法定繼承
財(cái)產(chǎn)的繼承分為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兩種方式。兩者之間的區(qū)別主要是:
(1)法定繼承是指按照法律規(guī)定的繼承人范圍、繼承順序和遺產(chǎn)分配原則進(jìn)行的繼承。遺囑繼承是指按被繼承人生前所立遺囑中指定的繼承人繼承其遺產(chǎn)所進(jìn)行的繼承。法定繼承是按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順序來進(jìn)行的;而遺囑繼承則是按財(cái)產(chǎn)所有人生前的意思來繼承的。
(2)法定繼承人的繼承份額是根據(jù)所有法定繼承人的情況和贍養(yǎng)扶養(yǎng)情況來確定的;遺囑繼承人的繼承份額是財(cái)產(chǎn)所有人在遺囑中確定的;
(3)遺囑繼承人必須是屬于法定繼承人范圍內(nèi)的人,而法定繼承人不一定都是遺囑繼承人。因?yàn)樵谶z囑繼承中,根據(jù)財(cái)產(chǎn)所有人的生前意愿,遺囑繼承人既可以是法定繼承人中的一人,也可以是法定繼承人中的若干人。哪些法定繼承人能夠繼承遺產(chǎn),這要取決于遺囑的內(nèi)容。
(4)我國(guó)實(shí)行遺囑繼承優(yōu)先于法定繼承的原則;也就是說,對(duì)公民個(gè)人遺產(chǎn)的繼承,如果財(cái)產(chǎn)所有人生前立有遺囑,只要該遺囑是合法有效的,必須按遺囑繼承,而不能按法定繼承。
三、遺囑繼承制度的缺陷
現(xiàn)階段主要表現(xiàn)在立法方面的缺陷
第一,保留必要的遺產(chǎn)份額的立法缺陷。
《繼承法》第19條規(guī)定:“遺囑應(yīng)當(dāng)對(duì)缺乏勞動(dòng)能力又沒生活來保留必要的遺產(chǎn)份額。”“高法意見 ”第37條規(guī)定:“遺囑人未保留缺乏勞動(dòng)能力又沒生活來源的繼承人的遺產(chǎn)份額,遺產(chǎn)處理時(shí),應(yīng)當(dāng)未該繼承人留下必要的遺產(chǎn),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參照遺囑確定的分配原則處理。繼承人是否缺乏勞動(dòng)能力有沒有生活來源,應(yīng)按遺囑生效時(shí)該繼承人的具體情況確定。”
立法作出這一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旨在保護(hù)缺乏勞動(dòng)能力又沒生活來源的繼承人的權(quán)益,以求法律的公正和社會(huì)財(cái)富分配的公平,其積極作用是無庸置疑的。但《繼承法》過于原則化的規(guī)定,是的在司法實(shí)踐中無法操作或在處理案件中違背立法原意,主要體現(xiàn)在:
首先,《繼承法》并未界定保留必要遺產(chǎn)份額的具體數(shù)額,賦予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
其次,在給予缺乏勞動(dòng)能力又沒生活來源的繼承人“必遺份”的特殊保護(hù)的同時(shí),對(duì)于在繼承完成后其他繼承人因生活中的變故而喪失勞動(dòng)能力又沒生活來源的情況沒有加以規(guī)定,對(duì)其他繼承人顯實(shí)公平。
最后,在全部遺產(chǎn)中,“必遺份”應(yīng)當(dāng)占有多少份額沒有界定,使得遺囑人在留出“必遺份”時(shí),因無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而無所適從,同時(shí)遺囑人對(duì)“必遺份”留出的多寡也可能導(dǎo)致繼承人之間產(chǎn)生糾紛,不利于家庭成員的和睦、團(tuán)結(jié)。
第二,遺囑執(zhí)行人制度的立法缺陷。
《繼承法》第十六條規(guī)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guī)定立遺囑處分個(gè)人財(cái)產(chǎn),并可以指定遺囑執(zhí)行人。”這種過于原則化的條款,在司法實(shí)踐中無法操作。
然而,遺囑執(zhí)行人制度在在外國(guó)的民事立法中都作了系統(tǒng)規(guī)定。如《意大利民法典》有十三條對(duì)遺囑執(zhí)行人的資格、任命、職責(zé)、權(quán)、遺產(chǎn)分割、帳目管理、遺囑執(zhí)行人的報(bào)酬作了詳盡的規(guī)定。我國(guó)臺(tái)灣民法對(duì)遺囑執(zhí)行人也規(guī)定了十條。[3]
四、遺囑繼承制度的完善
1.借鑒外國(guó)民法典“特留份”的法律制度
特留份制度,是指法律規(guī)定的遺囑人不得以遺囑的方式取消由特定的法定;繼承人繼承的遺產(chǎn)份額。該制度的實(shí)質(zhì)是通過對(duì)特定的法定繼承人規(guī)定一定的應(yīng)繼份額來限制遺囑人的遺囑自由,以法律的強(qiáng)制使得繼承人不必未爭(zhēng)得遺產(chǎn)而破壞家庭關(guān)系。
根據(jù)我國(guó)現(xiàn)行繼承法第28條和第29條規(guī)定,我國(guó)繼承法對(duì)遺囑自由的限制僅限于對(duì)胎兒保留必要的遺產(chǎn)份額和既缺乏勞動(dòng)能力又沒生活來源的“雙無人員”。這一限制過于寬泛,對(duì)法定繼承人缺乏保護(hù)力。相比較而言,特留份制度更具有優(yōu)越性。
《德國(guó)民法典》第2303條規(guī)定:“被繼承人的直接卑親屬因死因處分而被排除于繼承順序之外的,可以向繼承人請(qǐng)求特留份。特留份未法定應(yīng)繼份的價(jià)額的一半。被繼承人的父母和配偶因死因處分而被排除于繼承順序之外的,享有同樣的權(quán)利。”在法、比、意、荷、瑞士等國(guó)的民法中也對(duì)特留份制度做了具體規(guī)定,包括特留份權(quán)利人、數(shù)額、特留份請(qǐng)求權(quán)等。[4]
我國(guó)《繼承法》“必遺份”的規(guī)定應(yīng)修正為:“遺囑應(yīng)當(dāng)對(duì)缺乏勞動(dòng)能力又沒生活來源的第二順序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chǎn)份額”。將“必遺份”的范圍修正為第二順序繼承人,主要是使遺囑繼承法律制度與法定繼承法律制度加以協(xié)調(diào),繼承開始后,由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第二順序繼承人一般不繼承。沒有第一順序繼承人或第二順序繼承人對(duì)被繼承人盡了主要撫養(yǎng)義務(wù)的,得繼承。另外,還應(yīng)規(guī)定遺囑人采用贈(zèng)予方式規(guī)避“特留份”、“必遺份”的行為無效。
2.遺囑執(zhí)行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首先,應(yīng)對(duì)遺囑執(zhí)行人的資格加以規(guī)定。外國(guó)民法典大都規(guī)定禁治產(chǎn)人和未成年人不能作為遺囑執(zhí)行人。[5]我國(guó)法律應(yīng)規(guī)定遺囑執(zhí)行人應(yīng)當(dāng)具備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遺囑執(zhí)行人如系法人,法人必須出具授權(quán)委托書,指定1至2人參與遺囑的執(zhí)行。
其次,應(yīng)規(guī)定遺囑執(zhí)行人的產(chǎn)生方式。我國(guó)《繼承法》第十六條只規(guī)定了遺囑執(zhí)行人由遺囑直接指定的產(chǎn)生方式,因此由必要借鑒外國(guó)民事立法中遺囑執(zhí)行人的產(chǎn)生方式,即遺囑直接指定、遺囑委托指定、受理法院指定,以豐富《繼承法》遺囑執(zhí)行人的產(chǎn)生方式。
最后,應(yīng)明確遺囑執(zhí)行人的職責(zé)。如應(yīng)該規(guī)定:遺囑執(zhí)行人應(yīng)當(dāng)嚴(yán)格遵照遺囑人設(shè)立的遺囑處分遺產(chǎn),確保遺囑人的意愿得以執(zhí)行;遺囑執(zhí)行人為執(zhí)行遺產(chǎn)時(shí)可以占有遺產(chǎn),但遺囑執(zhí)行人由妥善保管遺產(chǎn)的義務(wù),遺囑執(zhí)行人應(yīng)在遺囑開始執(zhí)行時(shí),盡速將遺產(chǎn)得以執(zhí)行,有放棄繼承者,將其放棄繼承遺產(chǎn)份額登記造冊(cè),以便轉(zhuǎn)入法定繼承。[6]
參考文獻(xiàn):
[1]郭明瑞 房紹坤,繼承法[M],法律出版社九五系列
[2]梁學(xué)軍.時(shí)間:2005年2月20日16:26
[3]趙秉志.香港法律制度.北京:[M]中國(guó)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532頁
[4]自陳嬌.關(guān)于民法典繼承法編修改的幾點(diǎn)建議[M],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4年第3期
一、繼承公證概述
繼承公證是隨著社會(huì)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一種解決繼承問題的方式,為了更好探討繼承公證存在的風(fēng)險(xiǎn)以及采取何種措施避免這些風(fēng)險(xiǎn),需要首先明白繼承公證的一些基本內(nèi)容。
(一)繼承公證的概念
在我國(guó)民法中,繼承是指作為個(gè)體的公民死亡或者被法院宣告死亡后,依照相應(yīng)的程序?qū)⑺劳龌蛘弑恍嫠劳龅墓袼z留的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給繼承人所有的一種民事法律行為。按照法律規(guī)定,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在繼承關(guān)系中是被繼承人,而依照法律程序接受財(cái)產(chǎn)的公民則是繼承人。在民事法律關(guān)系中繼承制度是為了明確死者的財(cái)產(chǎn)應(yīng)當(dāng)如何處理的一種制度,而繼承公證是為了更好的保障繼承關(guān)系中的繼承行為所設(shè)立的一種公證制度,在實(shí)踐操作中,公證機(jī)構(gòu)辦理繼承公證時(shí)需要根據(jù)相應(yīng)的法律,比如《繼承法》、《婚姻法》等。
(二)繼承公證需要審查的基本內(nèi)容
在繼承關(guān)系中,公證的做出需要有一定的依據(jù),這就要求當(dāng)事人提供相應(yīng)的材料,由公證機(jī)構(gòu)進(jìn)行審查,提交的材料應(yīng)當(dāng)包括當(dāng)事人的身份證明原件及復(fù)印件、被繼承人的基本財(cái)產(chǎn)情況的證明、產(chǎn)權(quán)證明等、是否有遺囑及復(fù)印件,同時(shí)還有提供一些當(dāng)事人和被繼承人之間關(guān)系的證明。代位繼承人申辦公證的,還應(yīng)提供繼承人先于被繼承人死亡的證明及申請(qǐng)人與繼承人關(guān)系的證明,以及公證處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公證人員對(duì)當(dāng)事人提供的材料情況進(jìn)行審查,審查的基本內(nèi)容包括:首先是有關(guān)被繼承人死亡的相關(guān)情況,比如死亡的時(shí)間、地點(diǎn)、原因,同時(shí)還要審查被繼承人的遺留財(cái)產(chǎn)請(qǐng)況進(jìn)行詳細(xì)的審查,包括財(cái)產(chǎn)的數(shù)量、種類等,對(duì)被繼承人拖欠的稅款等款項(xiàng),按照相應(yīng)的法律法規(guī)辦理;其次是對(duì)是否有遺囑的情況作為重點(diǎn)進(jìn)行審查,如果有遺囑的,就要按照遺囑進(jìn)行辦理,不能違背被繼承人真實(shí)的意愿,如果沒有遺囑則要按照相關(guān)的法定程序做出公證。再次是審查當(dāng)事人是否屬于法定繼承人范圍內(nèi)的公民,繼承開始后,由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第二順序繼承人不繼承。沒有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的,由第二順序繼承人繼承。如果不是繼承人,則不予受理。最后是審查當(dāng)事人是否屬于代位繼承或轉(zhuǎn)繼承人。前者指繼承人先于被繼承人死亡時(shí),由繼承人的晚輩直系血親代位取得其應(yīng)繼承份額;后者指繼承人在被繼承人死亡之后、尚未實(shí)際接受遺產(chǎn)前死亡,可由繼承人的法定繼承人繼承其應(yīng)得遺產(chǎn)份額。公證人員應(yīng)依具體情況辦理上述公證。
二、繼承公證中存在的風(fēng)險(xiǎn)
繼承公證看似是一個(gè)公權(quán)力保障私權(quán)利的行為,但是由于社會(huì)中繼承關(guān)系的復(fù)雜以及各種問題的逐漸凸顯,因此繼承公證也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在本文中成為繼承公證的風(fēng)險(xiǎn),以下就對(duì)一些主要的風(fēng)險(xiǎn)展開闡述。
(一)遺產(chǎn)分割協(xié)議的合法性風(fēng)險(xiǎn)
當(dāng)事人要想通過公證機(jī)構(gòu)解決被繼承人的遺產(chǎn)問題,首先就是要向公證機(jī)構(gòu)提出申請(qǐng),用來證明遺產(chǎn)分割協(xié)議的真實(shí)且合法,這是公證機(jī)構(gòu)將遺產(chǎn)分割進(jìn)行公證的前提和依據(jù),為了更好的了解被繼承人情況和繼承人的情況,維護(hù)他們的基本權(quán)益,公證機(jī)構(gòu)應(yīng)當(dāng)盡量到遺產(chǎn)所在地或者繼承人較多的地方進(jìn)行相關(guān)事項(xiàng)的辦理和查證工作。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上述的申請(qǐng)要求提供相應(yīng)的資料或者委托證件等。公證機(jī)構(gòu)的工作人員在工作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相應(yīng)的法律法規(guī)要求,進(jìn)行相關(guān)事宜。但是,在審查和公證的工作中也應(yīng)當(dāng)注意一些問題,比如,遺產(chǎn)分割協(xié)議是否經(jīng)過每個(gè)人的同意或者認(rèn)可,對(duì)有遺囑的處理情況是否遵循了遺囑、有沒有照顧到胎兒的利益等,這都是需要解決的一些實(shí)踐存在的風(fēng)險(xiǎn)。
(二)法律適用存在的風(fēng)險(xiǎn)
一、遺體的法律地位
物權(quán)法、人身權(quán)法、親屬與繼承法是考慮遺體法律地位的三種主要法律語境。
遺體在物權(quán)法上的地位主要是可否將其認(rèn)定為物的問題。物權(quán)法是調(diào)整人對(duì)物以及特定權(quán)利的支配關(guān)系的法律規(guī)范。作為物權(quán)客體的物,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夠?yàn)槿肆χ淝夷軡M足人類某種需要的物質(zhì)。遺體是失去生命的人身,在人們的觀念中無法斷然割斷其與生者的倫理與情感聯(lián)系,但是根據(jù)上述物權(quán)法與物的概念,將遺體歸入物的范疇?wèi)?yīng)無大礙:遺體是物,死者近親屬對(duì)尸體享有所有權(quán),可以根據(jù)所有人的意志為醫(yī)學(xué)、科學(xué)研究等目的加以利用,但是權(quán)利的行使應(yīng)受公序良俗原則的限制。[1]
遺體在人身權(quán)法上的地位與死者的人身權(quán)益保護(hù)問題有關(guān)。我國(guó)現(xiàn)行法律沒有明確規(guī)定對(duì)死者人身權(quán)益的保護(hù),最高人民法院在此方面主要作出五項(xiàng)司法解釋[2],據(jù)此應(yīng)可解讀出以下三項(xiàng)基本原則,即(1)死者的人身權(quán)益應(yīng)予保護(hù)[3],(2)近親屬對(duì)死者的人身權(quán)益享有獨(dú)立的精神利益[4],(3)近親屬就死者人身權(quán)益實(shí)際享有并行使訴權(quán)[5].這種務(wù)實(shí)基調(diào)的三原則表明,司法實(shí)踐對(duì)有關(guān)死者人身權(quán)益保護(hù)問題的態(tài)度,似乎是在揚(yáng)棄死者本人的權(quán)利保護(hù)說與近親屬利益保護(hù)說的基礎(chǔ)上,采納了延伸保護(hù)說的立場(chǎng)。[6]由此似乎可以認(rèn)定,我國(guó)司法實(shí)踐對(duì)死者人身權(quán)益保護(hù)采取的是“保護(hù)逝者、救濟(jì)生者”的原則,即對(duì)因死者各項(xiàng)人身權(quán)益受到侵害而導(dǎo)致的近親屬的精神損害提供司法救濟(jì)。
對(duì)遺體產(chǎn)生的人身權(quán)益的規(guī)定見于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3條3款:“自然人死亡后,其近親屬因下列侵權(quán)行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訴請(qǐng)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依法予以受理:……(三)非法利用、損害遺體、遺骨,或者以違反社會(huì)公共利益、社會(huì)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遺體、遺骨。”該款規(guī)定明確了近親屬對(duì)遺體的獨(dú)立精神利益,以及遺體應(yīng)受社會(huì)公共利益與社會(huì)公德,即“公序良俗”保護(hù)的基本原則。按照以上所述三項(xiàng)原則以及對(duì)該條的體系解釋,將本款規(guī)定解為因侵害死者的身體權(quán)益而造成近親屬的精神損害,應(yīng)較妥當(dāng)。
據(jù)此,遺體既是死者延伸身體權(quán)益的載體,又是死者近親屬的特定精神利益的載體。強(qiáng)調(diào)前者的積極意義在于:(1)人皆不免一死,對(duì)自己遺體的繼續(xù)尊重應(yīng)屬絕大多數(shù)人的合理期待與要求,民法雖然應(yīng)著眼于現(xiàn)世,“事人不事鬼”,但也不能對(duì)尊重遺體的公序良俗漠然置之。所以,對(duì)遺體的保護(hù)符合作為生者的本人的利益。(2)果有不肖子孫因先祖遺體遭人踐踏而無動(dòng)于衷的,依據(jù)死者的延伸身體利益,一定范圍的其他親友或者組織也可以尋求救濟(jì),這種情況下的救濟(jì)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訴訟色彩與功能。(3)如此可以將對(duì)遺體的支配明確為權(quán)利人對(duì)其身體的延伸支配權(quán)范圍,權(quán)利人因而有權(quán)通過遺囑確定對(duì)遺體的處分方式,包括捐獻(xiàn)以及安葬方案。
遺體在親屬與繼承法上的地位首先是所有權(quán)的歸屬,第二是安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確定。
前者表現(xiàn)為遺體是否為遺產(chǎn)的爭(zhēng)論。[7]我國(guó)《繼承法》第3條規(guī)定,“遺產(chǎn)是公民死亡時(shí)遺留的個(gè)人合法財(cái)產(chǎn)”。人身在被繼承人生前是其人身利益,包括生命利益、身體利益、健康利益等的載體,不能被歸為物或者財(cái)產(chǎn)。人身因其死亡的事實(shí)而轉(zhuǎn)化為遺體之時(shí),被繼承人已因死亡而失去民事權(quán)利能力,不能再取得新的財(cái)產(chǎn),因而遺體不符合前述遺產(chǎn)須為被繼承人的“個(gè)人合法財(cái)產(chǎn)”的立法定義。據(jù)此,筆者認(rèn)為,遺體并非遺產(chǎn),而是因死亡的法律事實(shí)而產(chǎn)生的應(yīng)歸死者近親屬所有或者共有的物或者財(cái)產(chǎn);近親屬的范圍應(yīng)可參照《繼承法》上法定繼承人的范圍與順序加以確定。這種定位便于在死者本人未表示明確反對(duì)捐獻(xiàn)的情況下,其近親屬將遺體捐獻(xiàn)供作醫(yī)學(xué)或科學(xué)研究之用,從而有利于發(fā)揮遺體的價(jià)值。
現(xiàn)行《殯葬管理?xiàng)l例》是國(guó)務(wù)院頒布的行政法規(guī),主要從行政管理的角度對(duì)殯葬業(yè)進(jìn)行規(guī)范,并沒有明確近親屬對(duì)遺體或者骨灰的安葬權(quán)利或者義務(wù),只能另尋安葬權(quán)義的有關(guān)法源。我國(guó)《民法通則》沒有明確習(xí)慣的法律淵源地位,這可能是出于在改革開放政策初行之際,立法者有意通過法制建設(shè)來實(shí)施強(qiáng)制性社會(huì)變遷,或者至少在某些領(lǐng)域進(jìn)行移風(fēng)易俗的考慮。但是,即使在現(xiàn)代法治社會(huì),習(xí)慣對(duì)于和諧社會(huì)規(guī)則的形成與秩序的維系,實(shí)有發(fā)揮積極作用的廣泛空間。從憲法及民事法律的一些規(guī)定看,民事習(xí)慣也有一定的合法性空間。[8]實(shí)際上應(yīng)可以認(rèn)為,《民法通則》第7條“民事活動(dòng)應(yīng)當(dāng)尊重社會(huì)公德,不得損害社會(huì)公共利益……”的規(guī)定就表達(dá)了對(duì)習(xí)慣的尊重。因而可以說,遺體安葬權(quán)義的法源實(shí)際上是我國(guó)行之已久的民間殯葬習(xí)俗。根據(jù)各地的民間殯葬習(xí)俗,近親屬應(yīng)享有安葬死者的權(quán)利,或者負(fù)有安葬的義務(wù)。但是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是,法律對(duì)習(xí)慣的尊重具有一定的選擇性,不符合法律基本價(jià)值與政策的習(xí)慣無法得到認(rèn)可。本案中某甲遺體是否在祖墳?zāi)沟匕苍幔约皯?yīng)與“長(zhǎng)妻”抑或“次妻”合葬的問題,就面臨這一關(guān)的審視,容后再述。
根據(jù)以上的討論可以明確,遺體作為一種物,一種具有強(qiáng)烈社會(huì)倫理意義的特殊物,權(quán)利的行使應(yīng)受習(xí)慣(公序良俗)的限制;作為死者延伸身體利益的載體,在確定安葬方案時(shí)應(yīng)體現(xiàn)對(duì)其生前明示或者可得而知的意思的尊重;作為由死者近親屬享有所有權(quán)的物或者財(cái)產(chǎn)以及安葬權(quán)義的標(biāo)的,得由所有人或者共有人決定具體安葬方案。
二、遺囑確定遺體安葬方案的效力
根據(jù)上節(jié)的討論,在安葬方案的確定上可能存在來自習(xí)慣或者公序良俗、死者本人遺囑及其近親屬意志等至少三方面的競(jìng)爭(zhēng)與沖突。本節(jié)在分析通過遺囑確定遺體安葬方案的效力的過程中,探討對(duì)這些競(jìng)爭(zhēng)與沖突的解決之道。首先應(yīng)解決遺囑是否可用以安排身后的非財(cái)產(chǎn)事項(xiàng)?如果可以,則如何應(yīng)對(duì)另兩種因素的制約,現(xiàn)行法中有何可用的法制資源?
對(duì)身后的非財(cái)產(chǎn)事項(xiàng),包括決定遺體安葬方案,進(jìn)行安排的意思表示是否構(gòu)成遺囑?我國(guó)自古以來將遺囑稱為“遺命”、“遺令”、“遺言”,凡于生前對(duì)身后事宜處理所做的意思表示均為遺囑,包括立嗣、分產(chǎn)等身份與財(cái)產(chǎn)事項(xiàng)。[9]通過遺囑對(duì)身份事項(xiàng)作出安排已不符合與時(shí)俱進(jìn)的現(xiàn)代文明與法制要求,以之確定自己的遺體安葬方案實(shí)則大有人在。但是一則我國(guó)《繼承法》實(shí)際上只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繼承關(guān)系,二則如前所述遺體不構(gòu)成繼承法上的遺產(chǎn),故而這種遺囑似乎難以獲得繼承法意義上的遺囑地位。
對(duì)此有三種解決方案:一是拋開繼承法的窠臼,利用死者人身權(quán)益延伸保護(hù)的框架;二是根據(jù)民間殯葬習(xí)俗支持本人確定其安葬方案,同時(shí)訴諸移風(fēng)易俗的相關(guān)法律政策支持;三是仍在繼承法的框架內(nèi),通過推究“遺囑人”的本意,類推適用遺托制度,支持遺囑所作的遺體安葬方案。以
下依次分析。
就第一種方案來說,遺體是延伸身體利益的載體,權(quán)利人應(yīng)可以依法支配及處分。確定遺體的安葬方案與遺體捐獻(xiàn)均屬于遺體的具體處分方式。遺體捐獻(xiàn)在我國(guó)已經(jīng)大行其道,一些地方已制定相關(guān)地方法規(guī)。依照《上海市遺體捐獻(xiàn)條例》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遺體的捐獻(xiàn)生前由本人決定,并可隨時(shí)變更或者撤銷;死后可由其近親屬?zèng)Q定,但是以死者沒有明確反對(duì)為限[10].這已表明了對(duì)遺體的處分首先并且最終應(yīng)尊重本人意愿的原則立場(chǎng)。本人生前確定遺體的安葬方案既不違反公序良俗,也多有相關(guān)實(shí)踐,似乎沒有加以限制的充分理由,因而理應(yīng)尊重死者遺愿。這種“遺囑”自其作出有效意思表示時(shí)起成立,因其死亡而發(fā)生效力。
就第二種方案來說,根據(jù)民間殯葬習(xí)俗確認(rèn)近親屬的安葬權(quán)利與義務(wù),就應(yīng)黨對(duì)應(yīng)為死者生前得確定本人安葬方案的權(quán)利,只要不對(duì)近親屬造成過重負(fù)擔(dān),即應(yīng)受到尊重。
“移風(fēng)易俗的社會(huì)法律政策”從法律對(duì)土葬抑或火葬選擇的不同態(tài)度可見端倪。“積極地、有步驟地實(shí)行火葬,改革土葬”,是《殯葬管理?xiàng)l例》確定的殯葬管理方針之一(該條例第2條)。據(jù)此雖應(yīng)尊重少數(shù)民族或某些地區(qū)的土葬習(xí)俗,但該條例也明確規(guī)定,有自愿改革喪葬習(xí)俗的,他人不得干涉(該條例第6條)。地方法規(guī)《哈爾濱市殯葬管理?xiàng)l例》第5條2款規(guī)定:允許土葬的公民死亡后,凡本人生前留有遺囑或家屬自愿實(shí)行火葬的,任何人不得干涉。雖然此例規(guī)范目的限定,但是對(duì)當(dāng)事人選擇的尊重由此可見一斑。
此例同時(shí)也表明了法律不鼓勵(lì)不合時(shí)展趨勢(shì)、但又不宜強(qiáng)制除舊布新的某些傳統(tǒng)習(xí)俗。對(duì)本案當(dāng)事人因歷史而形成的一夫多妻狀況,法律即采這種態(tài)度。法律維持在1950《婚姻法》頒布施行前形成的一夫多妻狀況[11],但各妻之間有尊卑定分的舊制則因違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應(yīng)在摒棄之列。即使各地仍有習(xí)慣支持此種情況下某甲與“長(zhǎng)妻”合葬,某甲以遺囑明示與“次妻”合葬的,亦不失為“移俗善舉”,應(yīng)予尊重。
再看第三種繼承法框架的方案。我國(guó)《繼承法》第21條規(guī)定了附義務(wù)的遺囑繼承,即“遺托”:“遺囑繼承或者遺贈(zèng)附有義務(wù)的,繼承人或者受遺贈(zèng)人應(yīng)當(dāng)履行義務(wù)。沒有正當(dāng)理由不履行義務(wù)的,經(jīng)有關(guān)單位或者個(gè)人請(qǐng)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本案遺囑人僅通過遺囑對(duì)其安葬方案做出意思表示,未涉及遺產(chǎn)的處理,遺產(chǎn)的處理因而應(yīng)依照法定繼承辦理。但是須加考慮的實(shí)際情況是,遺囑人可能是因?yàn)椴涣私饫^承法的規(guī)定而為此種遺囑,這本身足以說明其非常重視所明示的安葬方案,以至于忽略了通過遺產(chǎn)繼承對(duì)子女加以制約。理想的方案固然是遺囑人當(dāng)時(shí)在法律專業(yè)人士的幫助下,設(shè)計(jì)一份簡(jiǎn)單明了而有效的附義務(wù)遺囑。但是在本案遺囑未對(duì)遺產(chǎn)分配做出安排的情況下,支持遺囑人指定的安葬方案,仍可在尊重逝者的意愿使其入土為安與保全生者的財(cái)產(chǎn)利益之間求得兩全。
為此,可以考慮類推適用遺托,將按遺囑人意愿進(jìn)行安葬認(rèn)定為法定繼承人接受繼承的條件。繼承人能夠履行該義務(wù)而無正當(dāng)理由不履行的,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3條的規(guī)定,得由提出請(qǐng)求的繼承人負(fù)責(zé)按遺囑人的意愿履行義務(wù),并接受遺產(chǎn)。
或謂,因?yàn)椴粓?zhí)行被繼承人指定的安葬方案而剝奪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結(jié)果是否稍過嚴(yán)厲?筆者以為,不能認(rèn)此過苛。因?yàn)椋阂粍t,在財(cái)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的繼承權(quán)與精神利益性質(zhì)的遺體安葬之間,無法斷然決出一般性的高下之別;二則,因無正當(dāng)理由不履行遺托義務(wù)而剝奪繼承權(quán)的,本來即僅以維護(hù)被繼承人通過遺囑表現(xiàn)的意志為本,并無對(duì)所附義務(wù)與繼承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之間的對(duì)比與考量;三則,繼承人在調(diào)解或者裁決過程中仍有機(jī)會(huì)改變其立場(chǎng),而竟固執(zhí)違逆遺囑人意志,甚至不惜喪失繼承權(quán)的,何足惜之?
三、近親屬對(duì)遺體安葬的精神利益
前述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3條3款明確了近親屬對(duì)遺體的獨(dú)立精神利益,但是僅限于近親屬有權(quán)禁止對(duì)遺體的非法利用或者侵害。該規(guī)定與有關(guān)遺體保護(hù)的學(xué)術(shù)討論均沒有涉及近親屬對(duì)遺體安葬的精神利益問題。 [12]揆其要點(diǎn),即使如前所述可以訴諸習(xí)慣確認(rèn)近親屬對(duì)遺體安葬的精神利益,仍需解決精神利益的內(nèi)容為何,以及在近親屬之間如何分配的問題。以下依次分析。
遺體安葬的精神利益至少包括兩方面內(nèi)容:一是參加葬禮,寄托與表達(dá)對(duì)死者的哀思;二是決定遺體的安葬方案[13].其中前者不具有獨(dú)占性,可由超過法定繼承人范圍的更多親屬共享;后者具有獨(dú)占性,將決定權(quán)限制在法定繼承人范圍內(nèi)較為妥當(dāng)。
葬禮制度可謂中華古代禮制的縮影。每個(gè)家族成員根據(jù)自己與死者的血緣親疏,在葬禮中分別穿著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等五種不同等級(jí)的喪服,“遵禮成服”,即為“五服”。現(xiàn)在雖然不能再依照五服舊制確定遺體安葬上的精神利益分配,卻不能不考慮近親屬間的親疏之別對(duì)此的影響。應(yīng)當(dāng)明確的是,勘定親疏之別并非要復(fù)活傳統(tǒng)舊制,而有其現(xiàn)實(shí)的倫理與生活基礎(chǔ);法律上的勘定是為了確定特定利益(包括財(cái)產(chǎn)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一般分配順序,不妨礙遺囑人另作安排。
這種親疏之別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構(gòu)成我國(guó)《繼承法》確定法定繼承人范圍與繼承順序的重要考慮因素:因婚姻而形成的夫妻關(guān)系是最初和最基本的家庭關(guān)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礎(chǔ),因而位列第一順序繼承人的首位;父母子女之間具有最近的直系血緣關(guān)系,具有最密切的人身與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但因成婚子女單獨(dú)成立家庭,形成相對(duì)獨(dú)立的家庭生活單元,故將子女列為次位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父母居于第三。類似但有別的情況是,確定精神病人的監(jiān)護(hù)人的順序?yàn)榕渑肌⒏改浮⒊赡曜优龋颂幜硗饧尤肓吮O(jiān)護(hù)能力的考量。[14]
對(duì)安葬上的精神利益分配順序可以參照法定繼承人的繼承順序確定如下:(1)因?yàn)閰⒓釉岫Y的精神利益在一般情況下具有可共享性,所以可以認(rèn)定第一順序與第二順序的法定繼承人以及按照殯葬習(xí)俗得參加葬禮的其他親屬對(duì)于安葬都享有精神利益,都有權(quán)參加死者的葬禮。(2)在死者沒有對(duì)安葬方案的明確意思表示的情況下,決定權(quán)或者參與表決權(quán)應(yīng)按照配偶、子女、父母等順序分配,前一順序繼承人的意思表示優(yōu)先并且排斥后一順序繼承人。(3)同一順序的繼承人享有平等的決定權(quán)。在繼承人如本案原被告般為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的情形中,各人對(duì)安葬方案的表決可能會(huì)宗其亡母的利益,由此可能會(huì)造成有利于子女眾多一方的結(jié)果。這一結(jié)果雖不能避免,但不宜再背離眾子女平等原則,將各表決權(quán)賦予不同權(quán)重,以免釀成僵局,又徒增生者間的爭(zhēng)訟。(4)同一順序的繼承人之間不能達(dá)成一致意見的,后一順序的繼承人得加入平等參與表決;(5)仍不能達(dá)成一致意見的,由居民委員會(huì)、村民委員會(huì)幫助調(diào)解,或者由人民法院裁決。
四、如何入土方為安:本案處理方案的選擇
總結(jié)本文所論,確定遺體安葬方案,應(yīng)建立在對(duì)遺體法律地位的認(rèn)識(shí)基礎(chǔ)上。根據(jù)本文的討論,遺體是一種具有強(qiáng)烈社會(huì)倫理意義的特殊物,權(quán)利的行使應(yīng)受習(xí)慣或者公序良俗原則的限制;作為死者延伸身體利益的載體,在確定安葬方案時(shí)應(yīng)尊重其生前明示或者可得而知的意思;作為由死者近親屬享有所有權(quán)的客體以及安葬權(quán)利義務(wù)的標(biāo)的,又得由所有人決定具體安葬方案。
從遺體作為所有權(quán)的客體出發(fā),固應(yīng)由所有權(quán)人確定安葬方案。但是本案中某甲的遺囑已經(jīng)指明具體的安葬方案,即應(yīng)排斥其近親屬,包括其與某乙、某丙生育的眾子女,在此方面另作安排,眾子女因此不再享有遺體安葬方案的決定權(quán)。雖然這種遺囑不構(gòu)成繼承法上旨在處理財(cái)產(chǎn)繼承事宜的典型遺囑,但是無論是從對(duì)死者的延伸身體權(quán)益保護(hù)的角度,
還是從民間殯葬習(xí)俗上的安葬權(quán)利義務(wù)的角度,或者對(duì)繼承法上的附義務(wù)繼承的類推適用角度,均應(yīng)支持這種“非典型”遺囑的效力,依照死者遺愿進(jìn)行安葬。
第一種固然屬于正本清源的最直接與干凈利索的方案,但是關(guān)于死者的人身權(quán)益保護(hù)在理論上仍存在一些爭(zhēng)議,有關(guān)司法解釋在死者本人的權(quán)利問題上又采取了“存而不論”的回避態(tài)度,因而會(huì)影響該方案在司法實(shí)踐中的可行性。
第二種方案牽涉到對(duì)習(xí)慣的司法認(rèn)可。在習(xí)慣的司法認(rèn)可問題上應(yīng)采取“集權(quán)式”的司法解釋認(rèn)可方式,還是“分權(quán)式”的個(gè)案審判實(shí)踐認(rèn)可方式,尚需明確。筆者謹(jǐn)慎地認(rèn)為,對(duì)于殯葬這樣一個(gè)有深厚傳統(tǒng)文化背景與廣泛實(shí)踐的領(lǐng)域,在沒有最高人民法院明確的司法解釋或者相關(guān)批復(fù)的情況下,法官在個(gè)案審判中根據(jù)《民法通則》第7條的規(guī)定認(rèn)可不違反法律基本價(jià)值的各地殯葬習(xí)俗,并以之確定當(dāng)事人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是具有可行性的。這也符合我國(guó)一直以來的習(xí)慣法“小傳統(tǒng)”,有助于使人們感受到法律與他們生活的密切性,有利于增強(qiáng)法律的親和性和感召力。[15]
第三種類推適用附義務(wù)遺囑繼承的方案,既符合本人的真實(shí)意思,也符合對(duì)人身權(quán)進(jìn)行周密保護(hù)的現(xiàn)代人權(quán)觀念,輔之以適當(dāng)?shù)恼{(diào)解與勸導(dǎo),一般不會(huì)發(fā)生斷然剝奪繼承權(quán)的嚴(yán)厲后果,應(yīng)當(dāng)說也具有較大的可行性。
注釋
[1] 參見李富成、常鵬翱:《“物”為何物:物權(quán)客體的界定》,《人民法院報(bào)》,2004年12月29日B1版。
[2] 參見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死亡人的名譽(yù)權(quán)應(yīng)受法律保護(hù)的函》(以下簡(jiǎn)稱“死亡人名譽(yù)保護(hù)函”)、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以下簡(jiǎn)稱“民法通則意見”)第161條、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名譽(yù)權(quán)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jiǎn)稱“名譽(yù)權(quán)案件解答”)第5項(xiàng)、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確定民事侵權(quán)精神損害賠償責(zé)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jiǎn)稱“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3條、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jiǎn)稱“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8條。
[3] 死亡人名譽(yù)保護(hù)函第一條規(guī)定:“吉文貞(藝名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譽(yù)權(quán)應(yīng)依法保護(hù),其母陳秀琴亦有權(quán)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民法通則意見第161條規(guī)定:“公民死亡后,其名譽(yù)受到侵害,使其配偶、父母、子女或者其他有關(guān)人員受到損害的,受害人可以提起訴訟。”;名譽(yù)權(quán)案件解答第5項(xiàng)規(guī)定:“死者名譽(yù)受到損害的,其近親屬有權(quán)向人民法院起訴。”;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3條規(guī)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親屬因下列侵權(quán)行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訴請(qǐng)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依法予以受理:(一)以侮辱、誹謗、貶損、丑化或者違反社會(huì)公共利益、社會(huì)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譽(yù)、榮譽(yù);(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隱私,或者以違反社會(huì)公共利益、社會(huì)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隱私;(三)非法利用、損害遺體、遺骨,或者以違反社會(huì)公共利益、社會(huì)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遺體、遺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8條規(guī)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親屬遭受精神損害,賠償權(quán)利人向人民法院請(qǐng)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確定民事侵權(quán)精神損害賠償責(zé)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確定。”以上各條規(guī)定均指明死者的人身權(quán)益為侵權(quán)對(duì)象(著重號(hào)為筆者所加)。
[4] 上注各項(xiàng)司法解釋中除第一項(xiàng)外,雖然均表明近親屬與死者人身權(quán)益之間在發(fā)生上的“連帶關(guān)系”,即近親屬因死者的人身權(quán)益受到侵害,而使自身受到損害,但據(jù)此似應(yīng)認(rèn)為其認(rèn)可近親屬對(duì)死者的人身權(quán)益享有獨(dú)立的精神利益,但對(duì)死者本人的人身權(quán)利至少采取了存而不論的態(tài)度。
[5] 上述死亡人名譽(yù)保護(hù)函第一條的用語為其母陳秀琴“亦有權(quán)”起訴外,其余各項(xiàng)司法解釋均徑行規(guī)定近親屬的訴權(quán)。這固然有從司法實(shí)踐的角度出發(fā),只能著眼于現(xiàn)世賦予生者訴權(quán)的考慮,實(shí)際上也回避了對(duì)死者訴權(quán)的爭(zhēng)議。如果僅認(rèn)可近親屬的訴權(quán),似乎對(duì)死者的人身權(quán)益保護(hù)的立場(chǎng)未盡徹底;如果從人身權(quán)延伸保護(hù)的角度出發(fā),似乎應(yīng)認(rèn)可死者的訴權(quán),以及近親屬的“代位”訴權(quán),也即近親屬作為人身權(quán)益“延伸保護(hù)的保護(hù)請(qǐng)求權(quán)人”(參見楊立新等:《人身權(quán)的延伸法律保護(hù)》,《法學(xué)研究》,1995(2),頁28;)。但是從以上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來看,似乎只認(rèn)可近親屬的獨(dú)立訴權(quán)。
[6] 關(guān)于三種學(xué)說的內(nèi)容,參見楊立新:《人格權(quán)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106—07.
[7] 參見郭明瑞、房紹坤:《繼承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頁94—95.
[8] 參見謝鴻飛:《論民事習(xí)慣在近現(xiàn)代民法中的地位》,《法學(xué)》,1998(3),頁31.
[9] 史尚寬:《繼承法論》,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頁395.
[10] 參見該條例第12、14條。
[11] 參見法制委員會(huì):《有關(guān)婚姻問題的若干解答》第一答問,《人民日?qǐng)?bào)》,1953年3月22日。
[12] 有關(guān)遺體的法律保護(hù)的討論,參見楊立新:《人格權(quán)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186—89.
[13] 本人基于身體權(quán)的延伸支配而確定其遺體的安葬方案,也屬于這一方面的內(nèi)容,本節(jié)不贅。
論文摘要 繼承權(quán)產(chǎn)生的爭(zhēng)議問題是一個(gè)重要且急需解決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有訴訟、調(diào)解、協(xié)商等多種方式。但是,這些方式都是在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以后所采取的補(bǔ)救措施,根據(jù)訴訟經(jīng)濟(jì)的原則,從爭(zhēng)議產(chǎn)生之前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fàn)幾h發(fā)生是減少訴訟資源浪費(fèi)并使法治深入人心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方式,因此,繼承權(quán)公證就應(yīng)運(yùn)而生。按照通常的理解,繼承權(quán)公證,是公證機(jī)構(gòu)根據(jù)當(dāng)事人的申請(qǐng),依法證明該公民有繼承死者遺留的個(gè)人合法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真實(shí)性、合法性的活動(dòng)。在法律中,繼承分為兩類:一種是法定繼承;另一種則是遺囑繼承。為了更好的闡釋繼承公證存在的一些風(fēng)險(xiǎn)和應(yīng)當(dāng)采取哪些防范措施有效的避免風(fēng)險(xiǎn),本文從實(shí)踐的角度出發(fā)展開論述和分析。
論文關(guān)鍵詞 繼承公證 存在風(fēng)險(xiǎn) 防范措施
繼承公證的基本概念毋庸累述,但是,在實(shí)踐操作中繼承公證需要重點(diǎn)重視的問題有哪些、需要從那些方向保障繼承公證實(shí)施的程序公證和實(shí)體公正,都是需要我們繼續(xù)研究和分析的內(nèi)容。做好繼承公證能夠有效的保護(hù)公民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構(gòu)建司法文明和社會(huì)文明,有效的穩(wěn)定社會(huì)發(fā)展。所以做好繼承公證方面的風(fēng)險(xiǎn)防范工作極為重要,在本文中,筆者從實(shí)踐研究者的角度對(duì)繼承公證的相關(guān)問題展開分析,對(duì)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論述和分析,并在論文的最后提出一些防范措施,力求使繼承公證這一行為能夠達(dá)到其應(yīng)有的效果,為社會(huì)的發(fā)展做出應(yīng)有的貢獻(xiàn)。
一、繼承公證概述
繼承公證是隨著社會(huì)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一種解決繼承問題的方式,為了更好探討繼承公證存在的風(fēng)險(xiǎn)以及采取何種措施避免這些風(fēng)險(xiǎn),需要首先明白繼承公證的一些基本內(nèi)容。
(一)繼承公證的概念
在我國(guó)民法中,繼承是指作為個(gè)體的公民死亡或者被法院宣告死亡后,依照相應(yīng)的程序?qū)⑺劳龌蛘弑恍嫠劳龅墓袼z留的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給繼承人所有的一種民事法律行為。按照法律規(guī)定,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在繼承關(guān)系中是被繼承人,而依照法律程序接受財(cái)產(chǎn)的公民則是繼承人。在民事法律關(guān)系中繼承制度是為了明確死者的財(cái)產(chǎn)應(yīng)當(dāng)如何處理的一種制度,而繼承公證是為了更好的保障繼承關(guān)系中的繼承行為所設(shè)立的一種公證制度,在實(shí)踐操作中,公證機(jī)構(gòu)辦理繼承公證時(shí)需要根據(jù)相應(yīng)的法律,比如《繼承法》、《婚姻法》等。
(二)繼承公證需要審查的基本內(nèi)容
在繼承關(guān)系中,公證的做出需要有一定的依據(jù),這就要求當(dāng)事人提供相應(yīng)的材料,由公證機(jī)構(gòu)進(jìn)行審查,提交的材料應(yīng)當(dāng)包括當(dāng)事人的身份證明原件及復(fù)印件、被繼承人的基本財(cái)產(chǎn)情況的證明、產(chǎn)權(quán)證明等、是否有遺囑及復(fù)印件,同時(shí)還有提供一些當(dāng)事人和被繼承人之間關(guān)系的證明。代位繼承人申辦公證的,還應(yīng)提供繼承人先于被繼承人死亡的證明及申請(qǐng)人與繼承人關(guān)系的證明,以及公證處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公證人員對(duì)當(dāng)事人提供的材料情況進(jìn)行審查,審查的基本內(nèi)容包括:首先是有關(guān)被繼承人死亡的相關(guān)情況,比如死亡的時(shí)間、地點(diǎn)、原因,同時(shí)還要審查被繼承人的遺留財(cái)產(chǎn)請(qǐng)況進(jìn)行詳細(xì)的審查,包括財(cái)產(chǎn)的數(shù)量、種類等,對(duì)被繼承人拖欠的稅款等款項(xiàng),按照相應(yīng)的法律法規(guī)辦理;其次是對(duì)是否有遺囑的情況作為重點(diǎn)進(jìn)行審查,如果有遺囑的,就要按照遺囑進(jìn)行辦理,不能違背被繼承人真實(shí)的意愿,如果沒有遺囑則要按照相關(guān)的法定程序做出公證。再次是審查當(dāng)事人是否屬于法定繼承人范圍內(nèi)的公民,繼承開始后,由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第二順序繼承人不繼承。沒有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的,由第二順序繼承人繼承。如果不是繼承人,則不予受理。最后是審查當(dāng)事人是否屬于代位繼承或轉(zhuǎn)繼承人。前者指繼承人先于被繼承人死亡時(shí),由繼承人的晚輩直系血親代位取得其應(yīng)繼承份額;后者指繼承人在被繼承人死亡之后、尚未實(shí)際接受遺產(chǎn)前死亡,可由繼承人的法定繼承人繼承其應(yīng)得遺產(chǎn)份額。公證人員應(yīng)依具體情況辦理上述公證。
二、繼承公證中存在的風(fēng)險(xiǎn)
繼承公證看似是一個(gè)公權(quán)力保障私權(quán)利的行為,但是由于社會(huì)中繼承關(guān)系的復(fù)雜以及各種問題的逐漸凸顯,因此繼承公證也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在本文中成為繼承公證的風(fēng)險(xiǎn),以下就對(duì)一些主要的風(fēng)險(xiǎn)展開闡述。
(一)遺產(chǎn)分割協(xié)議的合法性風(fēng)險(xiǎn)
當(dāng)事人要想通過公證機(jī)構(gòu)解決被繼承人的遺產(chǎn)問題,首先就是要向公證機(jī)構(gòu)提出申請(qǐng),用來證明遺產(chǎn)分割協(xié)議的真實(shí)且合法,這是公證機(jī)構(gòu)將遺產(chǎn)分割進(jìn)行公證的前提和依據(jù),為了更好的了解被繼承人情況和繼承人的情況,維護(hù)他們的基本權(quán)益,公證機(jī)構(gòu)應(yīng)當(dāng)盡量到遺產(chǎn)所在地或者繼承人較多的地方進(jìn)行相關(guān)事項(xiàng)的辦理和查證工作。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上述的申請(qǐng)要求提供相應(yīng)的資料或者委托證件等。公證機(jī)構(gòu)的工作人員在工作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相應(yīng)的法律法規(guī)要求,進(jìn)行相關(guān)事宜。但是,在審查和公證的工作中也應(yīng)當(dāng)注意一些問題,比如,遺產(chǎn)分割協(xié)議是否經(jīng)過每個(gè)人的同意或者認(rèn)可,對(duì)有遺囑的處理情況是否遵循了遺囑、有沒有照顧到胎兒的利益等,這都是需要解決的一些實(shí)踐存在的風(fēng)險(xiǎn)。
(二)法律適用存在的風(fēng)險(xiǎn)
公證機(jī)構(gòu)在對(duì)繼承關(guān)系進(jìn)行公證時(shí)需要運(yùn)用相關(guān)的法律法規(guī),比如婚姻法、民法通則等,但是,也應(yīng)當(dāng)看到在適用這些法律的過程中存在著法律適用風(fēng)險(xiǎn)的問題。按照法理學(xué)的相關(guān)理論,法律風(fēng)險(xiǎn)包括了法律之間的沖突、沒有有效立法和缺乏操作性等方面的問題。法律之間的沖突是由在立法過程中沒有充分協(xié)調(diào)和處理好相關(guān)承接關(guān)系造成的,也是公證機(jī)構(gòu)在辦理繼承公證時(shí)經(jīng)常遇到的一種風(fēng)險(xiǎn)。比如在實(shí)體法法律體系中,當(dāng)前的《繼承法》、《婚姻法》、《物權(quán)法》和最高院的《繼承法意見》都是公證機(jī)構(gòu)在辦理相關(guān)繼承公證時(shí)應(yīng)當(dāng)遵守的實(shí)體性規(guī)范,但是應(yīng)當(dāng)看到,《繼承法》是20世紀(jì)80年代的產(chǎn)物,歷時(shí)較長(zhǎng),而《婚姻法》則是在本世紀(jì)初制定,其對(duì)《繼承法》的一些內(nèi)容做出了修改,更加符合現(xiàn)展的理念,《物權(quán)法》的制定則據(jù)現(xiàn)代更近,2007年正式實(shí)施。因此,由于立法的時(shí)代不同,法律所解決問題的方式也存在著差異,那么面對(duì)這一現(xiàn)狀,如何解決,是采用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還是采用新法優(yōu)于舊法,時(shí)至今日,最高院或者立法機(jī)關(guān)都沒有做出統(tǒng)一的規(guī)定,這就造成了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出現(xiàn)矛盾或者沖突,造成公證機(jī)構(gòu)在公證時(shí)難以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法律沖突的另一個(gè)體現(xiàn)就是法律空白和法律缺乏可操作性的問題。比如我國(guó)的《繼承法》在上世紀(jì)制定,由于當(dāng)時(shí)問題的性質(zhì)與現(xiàn)代有很大不同,現(xiàn)代該法規(guī)定的內(nèi)容較為原則,缺乏現(xiàn)實(shí)可操作性,公證機(jī)構(gòu)辦理繼承公證,需要解決一系列復(fù)雜的問題,如果不能有明確且細(xì)致的法律進(jìn)行指導(dǎo),極有可能出現(xiàn)侵害當(dāng)事人權(quán)益的現(xiàn)象發(fā)生。因此對(duì)于公證機(jī)構(gòu)在辦理繼承公證時(shí)遇到的許多問題,至今仍處于探索階段。如怎樣認(rèn)定自然人有無遺囑、遺贈(zèng)扶養(yǎng)協(xié)議等。
總之,不論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或者規(guī)則作為指引,更何況是牽扯到社會(huì)公平正義和當(dāng)事人利益的繼承公證那,如果沒有相應(yīng)的規(guī)則進(jìn)行指導(dǎo),公證機(jī)構(gòu)的公信力將難以建立,公證質(zhì)量更難以保障,如果進(jìn)入訴訟階段,公證機(jī)構(gòu)將在繼承關(guān)系處理中失去話語權(quán),公民對(duì)公證機(jī)構(gòu)的任何度將會(huì)急劇下降。
(三)公證機(jī)構(gòu)的公證質(zhì)量風(fēng)險(xiǎn)
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應(yīng)當(dāng)是當(dāng)事人的誠(chéng)信觀念缺乏和證據(jù)、材料核實(shí)方式落后造成的。當(dāng)前我國(guó)雖然確立了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人們的思想認(rèn)識(shí)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那種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道德觀念依然存在,由于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思想和傳統(tǒng)道德出現(xiàn)交織,也造成了傳統(tǒng)的誠(chéng)信理念受到?jīng)_擊。另外,國(guó)家的立法不完善,地方政府對(duì)法治國(guó)家、和諧社會(huì)的理解不恰當(dāng),也對(duì)于當(dāng)事人的失信行為失之以寬、失之以軟,無原則地遷就,產(chǎn)生了嚴(yán)重的負(fù)面社會(huì)后果。面對(duì)這種失信行為,公證機(jī)構(gòu)在公證過程中將對(duì)一些問題難以做出抉擇,同時(shí)由于公證機(jī)構(gòu)在核查相關(guān)證據(jù)、材料時(shí),方式落后,比如在審核材料時(shí)依然采用傳統(tǒng)的政審方式,這就蘊(yùn)含著一定風(fēng)險(xiǎn),不符合現(xiàn)代型社會(huì)的要求和發(fā)展。
三、繼承公證風(fēng)險(xiǎn)防范的方法
針對(duì)繼承公證存在的風(fēng)險(xiǎn),為了更好的保障社會(huì)的穩(wěn)定,處理好繼承關(guān)系,維護(hù)各方利益,相關(guān)部門應(yīng)當(dāng)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盡量避免繼承公證的風(fēng)險(xiǎn),筆者從實(shí)踐的角度出發(fā),認(rèn)為可以從以下幾個(gè)方面進(jìn)行防范。
(一)提高意識(shí),轉(zhuǎn)變觀念
觀念的形成與人們的生活環(huán)境和生存歷史有很大關(guān)系,也是潛移默化、深入人心的一種內(nèi)容,因此,觀念指導(dǎo)人們的行為,轉(zhuǎn)變觀念是極為重要的。公證機(jī)構(gòu)應(yīng)當(dāng)充分認(rèn)識(shí)到這一情況,在公證過程中不僅僅要扮演著工作人員的角色,還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扮演專家的角色,為民眾提供一個(gè)真心的服務(wù),幫助他們熟悉與繼承有關(guān)的法律法規(guī),使他們能夠了解相關(guān)理論,在當(dāng)事人提供證據(jù)材料不全或者不會(huì)舉證時(shí),對(duì)他們進(jìn)行輔導(dǎo),指導(dǎo)他們根據(jù)要求收集證據(jù)。同時(shí),公證機(jī)構(gòu)還應(yīng)當(dāng)為民眾提供其他登記部門的登記事項(xiàng)和流程,使其能夠盡快的完成相關(guān)事項(xiàng)。在繼承公證辦理過程中,如果出現(xiàn)了一些棘手的問題,應(yīng)當(dāng)積極的與立法機(jī)構(gòu)和司法機(jī)關(guān)進(jìn)行有效的溝通和協(xié)調(diào),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shí)關(guān)注遺產(chǎn)稅的問題,為以后實(shí)施該政策提供幫助。
(二)深化告知義務(wù)、明確告知內(nèi)涵
我國(guó)《公證法》對(duì)公證機(jī)構(gòu)的告知義務(wù)進(jìn)行了明確規(guī)定,法律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規(guī)定,不是為了讓當(dāng)事人認(rèn)識(shí)到公證機(jī)構(gòu)已經(jīng)進(jìn)行了告知,也不是為了公證機(jī)構(gòu)在出現(xiàn)相關(guān)爭(zhēng)議時(shí)明確自己已經(jīng)完成了告知義務(wù),而是希望將這一義務(wù)職能化,將公證機(jī)構(gòu)工作人員的身份轉(zhuǎn)變?yōu)閷<胰说纳矸荩M最大可能的維護(hù)當(dāng)事人的利益,使其感到公證的公平合理性。同時(shí)筆者認(rèn)為,在日常義務(wù)進(jìn)行告知后,還應(yīng)當(dāng)對(duì)以下內(nèi)容進(jìn)行告知:第一,對(duì)于繼承人在婚姻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發(fā)生的繼承獲得的財(cái)產(chǎn)能否屬于夫妻共同財(cái)產(chǎn),這一內(nèi)容關(guān)系到公民在處理以后相關(guān)問題時(shí)解決方法,公證機(jī)構(gòu)在辦理公正的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明確。第二,就是關(guān)于繼承人獲得被繼承人遺產(chǎn)后的稅收問題要進(jìn)行告知。這是一項(xiàng)極為重要的內(nèi)容,因繼承人繼承不動(dòng)產(chǎn)可能需要繳納契稅、印花稅,在將繼承的不動(dòng)產(chǎn)對(duì)外銷售時(shí)可能會(huì)繳納個(gè)人所得稅,因個(gè)人所得稅、契稅涉及金額較大,而各地執(zhí)行該文件的情況不一,因此公證機(jī)構(gòu)應(yīng)告知繼承人到有關(guān)稅務(wù)機(jī)關(guān)了解稅務(wù)政策。第三,關(guān)于放棄繼承權(quán)或者遺產(chǎn)可能對(duì)放棄人產(chǎn)生的影響等問題要進(jìn)行明確告知。由于實(shí)踐中存在著各種復(fù)雜的情況,因此,有必要將上述內(nèi)容向當(dāng)事人詳細(xì)的告知,前一種放棄是對(duì)繼承權(quán)利的放棄,而后一種則是對(duì)所繼承的遺產(chǎn)進(jìn)行的直接放棄。對(duì)于放棄后的法律后果應(yīng)當(dāng)重點(diǎn)向當(dāng)事人說明,放棄后在公證機(jī)構(gòu)的公證中就不再享有相應(yīng)的權(quán)利,當(dāng)事人要想繼續(xù)獲得權(quán)利,只能訴至法院進(jìn)行解決。
(三)建立誠(chéng)信制度,完善核實(shí)方法
關(guān)鍵詞: 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 家庭承包 繼承法
中圖分類號(hào):DF52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3-8330(2014)02-0005-10
隨著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的活躍,訴至法院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糾紛逐漸增多。《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涉及農(nóng)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法釋[2005]6號(hào),以下簡(jiǎn)稱為《審理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解釋》)第1條將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繼承糾紛作為一種單獨(dú)的糾紛類型,并規(guī)定對(duì)涉及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繼承的糾紛,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依法受理。① 但在實(shí)體法上,對(duì)于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能否繼承的問題,我國(guó)現(xiàn)行法的規(guī)定并不明確;在當(dāng)下進(jìn)行的《繼承法》修訂中,對(duì)此問題應(yīng)如何處理也存在較大爭(zhēng)議。本文擬就此談些看法,期望對(duì)爭(zhēng)議的澄清和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既有的法律規(guī)定及學(xué)界爭(zhēng)論
(一)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能否繼承的既有規(guī)定
在我國(guó)1985年制定《繼承法》時(shí),對(duì)于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能否繼承的問題即存在激烈的爭(zhēng)論。② 最后通過的《繼承法》第4條規(guī)定:“個(gè)人承包應(yīng)得的個(gè)人收益,依照本法規(guī)定繼承。個(gè)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許由繼承人繼續(xù)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辦理。”最高人民法院的《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條規(guī)定:“承包人死亡時(shí)尚未取得承包收益的,可把死者生前對(duì)承包所投入的資金和所付出的勞動(dòng)及其增值和孳息,由發(fā)包單位或者接續(xù)承包合同的人合理折價(jià)、補(bǔ)償,其價(jià)額作為遺產(chǎn)。”上列規(guī)定中均區(qū)分收益與權(quán)利,僅規(guī)定個(gè)人承包的收益可以繼承,對(duì)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能否繼承則未予明確。③
1993年制定的《農(nóng)業(yè)法》第13條第4款雖然規(guī)定了“承包人在承包期內(nèi)死亡的,該承包人的繼承人可以繼續(xù)承包”,但在2002年底修訂時(shí)又將該規(guī)定刪除。就此來看,現(xiàn)行《農(nóng)業(yè)法》對(duì)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似持否定態(tài)度。
2003年實(shí)施的《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將土地承包區(qū)分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兩種,并在“家庭承包”一章的第31條規(guī)定:“承包人應(yīng)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繼承法的規(guī)定繼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繼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內(nèi)繼續(xù)承包。”另外,在“其他方式的承包”一章第50條規(guī)定:“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通過招標(biāo)、拍賣、公開協(xié)商等方式取得的,該承包人死亡,其應(yīng)得的承包收益,依繼承法的規(guī)定繼承;在承包期內(nèi),其繼承人可以繼續(xù)承包。”④該法繼受了《繼承法》第4條規(guī)定的精神,區(qū)別收益與權(quán)利,并進(jìn)一步區(qū)分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不同類型和承包地的類別,予以區(qū)別對(duì)待。其中,家庭承包中的林地承包人和其他方式承包中的“四荒”地的承包人死亡的,其繼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內(nèi)繼續(xù)承包。關(guān)于“繼承人可以繼續(xù)承包”的含義有兩種解釋:一是將其解釋為合同主體的變更,非為繼承法意義上的繼承;⑤ 二是解釋為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⑥ 筆者認(rèn)為后一理解更為符合現(xiàn)行法的立法精神。⑦ 因?yàn)榍罢咭酝恋爻邪?jīng)營(yíng)權(quán)是債權(quán)為基礎(chǔ),后者以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物權(quán)為基礎(chǔ),而《物權(quán)法》已肯定了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物權(quán)屬性;另外,如果不屬于繼承問題,則“可以繼續(xù)承包”的主體在表述上也不必限定為“繼承人”。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的《審理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解釋》第25條中,依據(jù)既有法律規(guī)定,承認(rèn)了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和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而對(duì)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則明確持否定態(tài)度。⑧
2007年實(shí)施的《物權(quán)法》中,設(shè)專章規(guī)定了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明確其為用益物權(quán)的一種,且規(guī)定該項(xiàng)權(quán)利可以多種方式流轉(zhuǎn),但對(duì)其能否繼承的問題,則采取了回避態(tài)度,未作明文規(guī)定。
(二)學(xué)界對(duì)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能否繼承問題的爭(zhēng)論
制定法層面的模糊與回避為學(xué)界的討論留下了空間。對(duì)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否能構(gòu)成繼承權(quán)的客體,學(xué)界存在肯定說和否定說兩種不同的觀點(diǎn)。
1.肯定說及其主要理由
肯定說實(shí)際上又可細(xì)分為三種主張:其一,不區(qū)分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類型,均可以作為繼承權(quán)的客體。如有學(xué)者主張,“繼承權(quán)的客體不僅僅局限于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和通過招標(biāo)、拍賣、公開協(xié)商等方式取得的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還應(yīng)當(dāng)包括耕地、草地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⑨“應(yīng)賦予農(nóng)民對(duì)包括耕地在內(nèi)的一切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以繼承權(quán)(法律有特殊規(guī)定或合同有特別約定的除外),只要在登記簿上進(jìn)行必要的變更登記即可”。⑩ 梁慧星教授主持?jǐn)M定的《中國(guó)物權(quán)法草案建議稿》中還對(duì)農(nóng)地使用權(quán)繼承中的具體問題提出了處理方案。B11其二,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原則上均可以繼承,但應(yīng)區(qū)分家庭承包與非家庭承包的不同情況:非家庭的個(gè)人承包(包括個(gè)人為一“戶”的情況),在承包人死亡時(shí),其個(gè)人享有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本身就是遺產(chǎn),可以繼承;而家庭承包中的部分戶內(nèi)成員死亡時(shí),發(fā)生的是具有共有關(guān)系的成員之間的份額權(quán)的繼承問題;發(fā)生“絕戶”情況時(shí),則按照類似于法人的清算終止程序處理。B12其三,認(rèn)為個(gè)人享有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以繼承,而家庭承包的情況則另當(dāng)別論。如楊立新、楊震教授擔(dān)綱的“繼承法修正案草案建議稿課題組”擬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繼承法〉修正草案建議稿》第7條即規(guī)定:遺產(chǎn)是被繼承人死亡時(shí)遺留的個(gè)人財(cái)產(chǎn),包括“個(gè)人享有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和承包收益”。B13此外,在肯定說中,有人主張應(yīng)對(duì)繼承人范圍予以限制,即非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繼承人不得繼承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但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應(yīng)堅(jiān)持“繼承平等”原則。B14
肯定論者的主要理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diǎn):
第一,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一種用益物權(quán),在承包人死亡后,法律應(yīng)當(dāng)允許其繼承人繼承。B15“物權(quán)法把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明確規(guī)定為用益物權(quán)的一個(gè)種類后,應(yīng)當(dāng)說,妨礙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繼承的法理障礙已徹底清除”。B16
第二,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一種財(cái)產(chǎn)權(quán),法律既然承認(rèn)其可以多種方式流轉(zhuǎn),亦應(yīng)允許繼承。“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作為公民的一項(xiàng)重要財(cái)產(chǎn)權(quán),應(yīng)當(dāng)可以繼承。承認(rèn)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以以轉(zhuǎn)包、出租、互換、轉(zhuǎn)讓、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轉(zhuǎn),也應(yīng)當(dāng)可以繼承。欠缺繼承性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就某種意義上說屬于不完整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也是難以順利流轉(zhuǎn)的。”B17
第三,考察域外法制和我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需要,應(yīng)當(dāng)允許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繼承。如有學(xué)者提出,無論是大陸法系的德國(guó)、法國(guó),還是英美法系的英國(guó)、美國(guó)和印度,及我國(guó)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和臺(tái)灣地區(qū),農(nóng)地使用權(quán)都是可以繼承的。從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險(xiǎn)的角度考量,允許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繼承,也符合我國(guó)客觀現(xiàn)實(shí)的需要。B18
2.否定說及其主要理由
早期的否定說系根據(jù)《繼承法》的規(guī)定精神,認(rèn)為僅承包收益可以繼承,而承包的客體、承包合同和承包權(quán)均不得當(dāng)作遺產(chǎn)而繼承,理由是:第一,作為承包合同標(biāo)的的農(nóng)村土地不是承包人的私有財(cái)產(chǎn),其屬于集體所有,承包人并不享有所有權(quán),根本不發(fā)生繼承問題;第二,承包合同關(guān)系是不能繼承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合同因當(dāng)事人一方死亡而終止,不發(fā)生繼承問題;第三,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基于承包合同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經(jīng)營(yíng)管理權(quán),而非財(cái)產(chǎn)權(quán),不屬于財(cái)產(chǎn)繼承的范圍,故此種權(quán)利不能繼承。B19
在《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quán)法》頒行后,繼承否定說主要系針對(duì)家庭承包的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而言。如有學(xué)者認(rèn)為,家庭承包方式獲得的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只能屬于農(nóng)戶家庭,而不可能屬于某一個(gè)家庭成員。根據(jù)《繼承法》第3條的規(guī)定,遺產(chǎn)是公民死亡時(shí)遺留的個(gè)人合法財(cái)產(chǎn),而“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不屬于個(gè)人財(cái)產(chǎn),故不發(fā)生繼承問題”。B20還有學(xué)者指出,“農(nóng)地使用權(quán)可以繼承”的理由不夠充分。首先,雖然土地使用權(quán)是農(nóng)民擁有的最大宗財(cái)產(chǎn)之一,但作為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繼承人可以依據(jù)自己的集體組織成員權(quán),取得維持其生存的土地使用權(quán),作為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繼承人則有城市保障體系的保證。而對(duì)于新增加的農(nóng)業(yè)人口,如果無法保障其土地使用權(quán),則可能危及其生存問題。其次,隨著農(nóng)民子女的擇業(yè)自由和擇業(yè)范圍的擴(kuò)大,農(nóng)地使用權(quán)可能因繼承事實(shí)的發(fā)生而轉(zhuǎn)移到非農(nóng)業(yè)人口手中,這顯然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與農(nóng)業(yè)的有效發(fā)展。B21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解釋》的闡釋書中也明確指出:《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將土地承包確定為家庭承包及其他方式承包兩種承包形式。家庭承包是以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內(nèi)部的農(nóng)戶家庭為單位、人人有份的家庭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福利性及生活保障性,將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作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的一項(xiàng)權(quán)利。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是以集體成員權(quán)為前提的;此種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具有社會(huì)保障功能,它為集體成員提供基本的社會(huì)保障。因此,如果依照繼承法的一般原理承認(rèn)其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則會(huì)對(duì)承包地的社會(huì)保障功能產(chǎn)生消極的影響;如果這種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由村集體外部的人取得,將會(huì)損害村集體內(nèi)部社會(huì)保障的基礎(chǔ),對(du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其他成員的權(quán)益造成損害。B22
3.簡(jiǎn)單的評(píng)述
肯定說側(cè)重于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物權(quá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屬性,認(rèn)為既然承認(rèn)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一種用益物權(quán),可以轉(zhuǎn)讓或以其他方式流轉(zhuǎn),就應(yīng)當(dāng)肯定包括家庭承包方式在內(nèi)的各類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以作為繼承的客體。但其忽略或者說回避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主體身份限制和功能的特殊性。就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流轉(zhuǎn)而言,我國(guó)法律雖然承認(rèn)了其可以包括轉(zhuǎn)讓在內(nèi)的多種方式流轉(zhuǎn),但《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第41條對(duì)轉(zhuǎn)讓的條件、程序和受讓人都有嚴(yán)格的限制,而非可以自由轉(zhuǎn)讓。因此,不能簡(jiǎn)單地認(rèn)為立法既然允許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轉(zhuǎn)讓,就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其可以繼承。如果允許家庭承包方式下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繼承,則會(huì)造成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外流或部分成員獲得兩份或多份承包地,而本應(yīng)得到承包地的成員卻得不到承包地,從而背離農(nóng)地的社會(huì)保障功能,這是不符合現(xiàn)行法的立法精神的。
否定說的有些理由產(chǎn)生于《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quán)法》頒行之前,顯然已經(jīng)過時(shí)而喪失了說服力。而有學(xué)者所持的“家庭承包方式獲得的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只能屬于農(nóng)戶家庭,而不可能屬于某一個(gè)家庭成員”的觀點(diǎn)也過于絕對(duì),因?yàn)楝F(xiàn)實(shí)生活中的確存在個(gè)人為一戶的現(xiàn)象,且不能排除原來的戶內(nèi)家庭成員因死亡而僅余一人或全部死亡的情況。唯有從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特殊性角度闡釋的理由,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在這方面,繼承否定論者挖掘得還有不足,被重視的程度也不夠。
筆者認(rèn)為,欲探究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能否作為繼承的客體并發(fā)生繼承問題,必須區(qū)分不同的承包方式來討論;而否定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則須從此種權(quán)利的主體限制及功能特點(diǎn)入手進(jìn)行深入分析。
二、不同承包方式下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主體與功能的差異
(一)不同承包方式下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主體之不同
“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者為種植、養(yǎng)殖、畜牧等農(nóng)業(yè)目的對(duì)其依法承包的農(nóng)民集體所有或國(guó)家所有由農(nóng)民集體使用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權(quán)利”。B23根據(jù)《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的規(guī)定,我國(guó)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按照人人平等、民主協(xié)商、公平合理原則而對(duì)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所采用的“家庭承包”;另一種是對(duì)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農(nóng)地通過招標(biāo)、拍賣、公開協(xié)商等方式建立的“其他方式的承包”。B24以不同方式獲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其主體即“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人”也有不同。《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第15條規(guī)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農(nóng)戶。”第41條規(guī)定,在農(nóng)戶轉(zhuǎn)讓通過家庭承包方式獲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時(shí),受讓方也應(yīng)當(dāng)是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農(nóng)戶。可見,家庭承包方式下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以成員權(quán)為基礎(chǔ),其具有較強(qiáng)的身份性。農(nóng)村集體組織成員身份既是取得家庭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必要條件,又是充分條件。B25根據(jù)《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第47、48條的規(guī)定,通過其他方式獲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其主體可以是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成員,B26亦可以是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gè)人,但后者要想取得“四荒”等農(nóng)地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除須尊重前者享有的在同等條件下的優(yōu)先承包權(quán)外,還須經(jīng)多數(shù)村民的同意,并報(bào)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批準(zhǔn)。
(二)不同承包方式下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功能之差異
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雖然是一種用益物權(quán)和一種財(cái)產(chǎn)權(quán),但其具有一定的身份性。B27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身份性在發(fā)包階段和流轉(zhuǎn)階段均有體現(xiàn)。B28賦予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一定身份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guó)還未全面建立農(nóng)村社會(huì)保障制度,農(nóng)村土地仍然承載著社會(huì)保障功能,優(yōu)先保障農(nóng)民的基本生活需要。B29限制非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人員獲得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以緩解大量的農(nóng)村人口和有限的土地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需要指出的是,家庭方式承包獲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具有較強(qiáng)的福利性和社會(huì)保障功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一種特殊用益物權(quán),該種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取得以集體成員權(quán)為基礎(chǔ),雖然經(jīng)濟(jì)組織以外成員可通過其他承包方式獲得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但是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以外的成員承包土地與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內(nèi)部的農(nóng)民取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在程序和權(quán)利范圍等方面都是有區(qū)別的。B30以不同的承包方式獲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其社會(huì)保障功能的強(qiáng)弱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第一,從對(duì)主體的限定中可以看出,在家庭承包方式下,無論是發(fā)包階段的承包方,抑或是轉(zhuǎn)讓時(shí)的受讓方,都只能是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農(nóng)戶。而四荒地的承包方或受讓方則無此種限定。
第二,從取得方式上看,由于家庭承包負(fù)載著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的基本社會(huì)保障功能,所以其應(yīng)遵循人人平等、民主協(xié)商、公平合理的原則進(jìn)行;而四荒地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幾乎不負(fù)載社會(huì)保障功能,故可以引入招標(biāo)、拍賣、公開協(xié)商等商業(yè)化的取得方式,通過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最大化地發(fā)揮四荒土地資源的價(jià)值。
第三,家庭承包的土地主要是耕地、林地和草地,承包地本身關(guān)乎農(nóng)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主要是“四荒地”等不適宜家庭承包的土地,其與農(nóng)民的生存需要關(guān)系不大。
第四,是否需繳納稅費(fèi)不同。我國(guó)自2006年取消了農(nóng)業(yè)稅后,農(nóng)民種地不需再繳納各種稅費(fèi),而且還會(huì)得到不同的補(bǔ)貼;而以其他方式承包,則需繳納有關(guān)稅費(fèi)。
第五,從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流轉(zhuǎn)的規(guī)定中,亦可窺見立法精神的差異。根據(jù)《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第41條的規(guī)定,以家庭承包方式獲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在轉(zhuǎn)讓時(shí),應(yīng)當(dāng)符合以下條件:1.轉(zhuǎn)讓方有穩(wěn)定的非農(nóng)職業(yè)或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2.經(jīng)發(fā)包方同意;3.受讓方應(yīng)當(dāng)是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農(nóng)戶。而通過其他方式獲得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轉(zhuǎn)讓,法律未作如此限定。除了轉(zhuǎn)讓外,我國(guó)法律還許可將“四荒”地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抵押,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由于更側(cè)重其社會(huì)保障功能,因而法律未允許抵押。
綜上,雖然兩種承包方式下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主體均具有一定的身份性,但是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權(quán)的身份性是絕對(duì)的,招標(biāo)、拍賣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身份性是相對(duì)的(《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僅在第47條中強(qiáng)調(diào)規(guī)定了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同等條件下的優(yōu)先承包權(quán));前者承載著較強(qiáng)的福利性和社會(huì)保障功能,而后者的福利性及社會(huì)保障功能較為薄弱。由于作為遺產(chǎn)的條件之一必須是非專屬性的,可以在不同主體之間自由轉(zhuǎn)讓。B31而不同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所存在的上述差異,直接決定了其是否可作為遺產(chǎn)。
三、家庭承包中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問題
家庭承包中的“農(nóng)戶”是一個(gè)集合概念,它以農(nóng)村人口戶籍管理中的“戶”為基本單位。戶內(nèi)的成員可以是多個(gè)家庭成員,也可以僅為一人;且戶內(nèi)成員處在一個(gè)流動(dòng)狀態(tài),可能增加,亦可能減少。農(nóng)戶中的成員共同享有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只要農(nóng)戶存在,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即存續(xù),不受農(nóng)戶成員數(shù)量變化的影響。因此,當(dāng)由多個(gè)成員組成的農(nóng)戶作為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主體時(shí),戶內(nèi)一個(gè)或部分成員的死亡,不發(fā)生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終止及繼承問題,只有當(dāng)該戶內(nèi)成員全部死亡或者一人為一戶的成員死亡時(shí),才存在其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否終止或能否繼承的問題。
(一)家庭成員部分死亡的效果
根據(jù)法律和相關(guān)政策規(guī)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農(nóng)戶”,該農(nóng)戶通常由在一個(gè)家庭共同生活的數(shù)個(gè)成員組成;每戶承包土地的面積多少,根據(jù)發(fā)包當(dāng)時(shí)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內(nèi)農(nóng)戶的數(shù)量、戶內(nèi)人口的數(shù)量和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農(nóng)用土地面積,按比例平等分配。如此,以“農(nóng)戶”為單位取得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在該戶內(nèi)成員之間形成共有關(guān)系。依據(jù)“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原則,當(dāng)農(nóng)戶中的某一個(gè)或部分成員死亡時(shí),不發(fā)生繼承問題,而只會(huì)產(chǎn)生生存的戶內(nèi)成員權(quán)利份額的自然擴(kuò)張,比如四口人的農(nóng)戶變成三口人的農(nóng)戶,每個(gè)成員的份額由原來的四分之一自然地?cái)U(kuò)張為三分之一。農(nóng)戶中的部分成員死亡,該農(nóng)戶中的其他成員在承包期內(nèi)繼續(xù)承包,這不是繼承,而是按照承包合同的約定繼續(xù)履行承包合同的行為。B32有人把這種在剩余承包期內(nèi)的繼續(xù)承包看做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實(shí)際上是一種誤解。而對(duì)這一問題的準(zhǔn)確理解,首先須明確農(nóng)戶成員對(duì)其共同享有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究竟是一種什么關(guān)系。
筆者認(rèn)為,作為同一農(nóng)戶的家庭成員對(duì)其取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一種“準(zhǔn)共有”關(guān)系。所謂準(zhǔn)共有,是指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的主體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所有權(quán)以外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我國(guó)《物權(quán)法》在“共有”一章第105條對(duì)準(zhǔn)共有問題規(guī)定:“兩個(gè)以上單位、個(gè)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權(quán)、擔(dān)保物權(quán)的,參照本章規(guī)定。”由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以家庭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共有,因此應(yīng)是一種共同共有關(guān)系,故應(yīng)準(zhǔn)用法律關(guān)于共同共有的規(guī)定。但需注意的是,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這種以“戶”為單位的準(zhǔn)共有,具有其特殊性,即因?yàn)樵擁?xiàng)權(quán)利的福利性和社會(huì)保障功能,其主體資格具有嚴(yán)格的限定,并非任何人均有資格成為準(zhǔn)共有人。另根據(jù)《物權(quán)法》第99條的規(guī)定,一般情況下,在共同共有的基礎(chǔ)喪失之前,共同共有人不得請(qǐng)求分割共有物。在家庭承包關(guān)系中,成員部分死亡,只要作為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主體的農(nóng)戶家庭還存在,則共有的基礎(chǔ)關(guān)系即存在,其他共同共有人即不得請(qǐng)求分割共有物。根據(jù)舉輕以明重的解釋規(guī)則,死者的繼承人更不得請(qǐng)求繼承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即使農(nóng)戶中僅剩下一個(gè)成員,該成員也應(yīng)當(dāng)構(gòu)成一個(gè)承包經(jīng)營(yíng)戶。B33還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準(zhǔn)共有中的基礎(chǔ)關(guān)系不同于家庭普通財(cái)產(chǎn)共有中的基礎(chǔ)關(guān)系,前者體現(xiàn)為“農(nóng)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形式性。比如夫妻一方死亡,夫妻關(guān)系即告消滅,死亡一方的繼承人可以要求繼承其在普通共同財(cái)產(chǎn)中的相應(yīng)份額,但是卻不得主張對(duì)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因?yàn)殡m然夫妻一方死亡,但是作為承包主體的“戶”還存在。同理,已經(jīng)“分戶”出去的其他近親屬,屬于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的,自然也有其承包地和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該戶內(nèi)的成員部分死亡的,也依照同樣精神處理。依據(jù)“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原則,既不存在戶內(nèi)成員之間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繼承問題,更不存在“跨戶繼承”另一戶內(nèi)成員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問題。
承包期內(nèi),農(nóng)戶中的成員部分死亡,除了死亡成員的繼承人不得要求繼承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外,發(fā)包方亦不得因?yàn)檗r(nóng)戶中的部分成員死亡而收回相應(yīng)的承包地。根據(jù)“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原則和《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第26、27條的規(guī)定,除有法定情形外,在承包期內(nèi)發(fā)包方不得收回或者調(diào)整承包地,而承包戶中部分成員的死亡,不屬于收回或調(diào)整承包地的法定情形。
(二)家庭成員全部死亡的效果
農(nóng)戶中的成員全部死亡,該戶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及其與發(fā)包人的承包合同即因承包方主體的消亡歸于終止,其原承包的農(nóng)地應(yīng)收歸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并可另行分配,而不能由該農(nóng)戶成員的其他繼承人繼承或繼續(xù)承包經(jīng)營(yíng)。之所以對(duì)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進(jìn)行限制,也是基于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身份性和社會(huì)保障功能。B34同樣的道理,城市中生活困難的市民領(lǐng)取低保的資格和權(quán)益,其繼承人不得繼承;經(jīng)濟(jì)適用住房房主的繼承人不符合申購(gòu)條件的,不得繼承經(jīng)適房,唯可以繼承由政府回購(gòu)所得價(jià)款。在承包期內(nèi),承包戶中的成員全部死亡,有權(quán)繼承其遺產(chǎn)的其他繼承人如果隸屬于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包括隸屬于本村集體和遷入其他村集體),則其在“分戶”或另行立戶后已單獨(dú)分得了承包地,再跨戶繼承其他戶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實(shí)質(zhì)等于其獲得了兩份福利和社會(huì)保障;而如果繼承人已經(jīng)喪失了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的身份取得了城市戶口,則其本已享受了城市居民的福利和社會(huì)保障,其同樣無理由再通過繼承的方式獲得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huì)保障。因此,在承包戶中的成員全部死亡的情況下,如果允許其他繼承人繼承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則無論如何都會(huì)造成繼承人獲得兩份承包地或城市居民取得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現(xiàn)象。而從法理和社會(huì)公平的角度講,任何人均無由獲得兩份社會(huì)福利和基本社會(huì)保障,尤其是不應(yīng)享有具有不同身份屬性的雙重社會(huì)保障。故此,在某一承包戶發(fā)生絕戶情況時(shí),如果允許其他繼承人繼承其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既明顯違背農(nóng)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初衷和導(dǎo)向,也會(huì)加劇農(nóng)村中的人地矛盾,引發(fā)社會(huì)不公。
需要指出的是,承包人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不得作為遺產(chǎn)而發(fā)生繼承問題,但根據(jù)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因承包經(jīng)營(yíng)所取得的收益,應(yīng)區(qū)別于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本身,可以作為被繼承人的遺產(chǎn);死者生前對(duì)承包地所投入的資金和所付出的勞動(dòng)及其增值和孳息,應(yīng)由發(fā)包單位或者接續(xù)承包合同的人合理折價(jià)、補(bǔ)償,其價(jià)額屬于遺產(chǎn)。此外,在承包戶內(nèi)成員全部死亡時(shí),由于其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歸于消滅,故在承包期內(nèi)發(fā)生轉(zhuǎn)包、出租、入股等關(guān)系,也隨之歸于終結(jié),但承包人轉(zhuǎn)包、出租、入股所應(yīng)得的轉(zhuǎn)包費(fèi)、租金、股息等法定孳息,也屬于遺產(chǎn),可以由繼承人繼承。
另應(yīng)說明的是,在承包戶中的成員全部死亡時(shí),本應(yīng)由發(fā)包方收回該土地,但是實(shí)踐中,由于種種原因,存在著作為發(fā)包方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不積極行使權(quán)利而任由承包戶的繼承人占有并經(jīng)營(yíng)土地的情況。但這種個(gè)別現(xiàn)象的存在,并不說明法律上認(rèn)可了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可繼承性。B35
通過家庭承包方式獲得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原則上不得作為遺產(chǎn),但是《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規(guī)定了一種例外,該法第31條第2款規(guī)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繼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內(nèi)繼續(xù)承包。”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解釋》第25條也規(guī)定: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繼承人請(qǐng)求在承包期內(nèi)繼續(xù)承包的,應(yīng)予支持。據(jù)此規(guī)定的精神,通過家庭承包方式獲得的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以繼承。法律規(guī)定此種例外的原因是“林地的承包期較長(zhǎng)、投資大、收益慢,另外林木所有權(quán)的繼承與林地不能分離,如果不允許林地繼承,不利于調(diào)動(dòng)承包人的積極性,還可能會(huì)造成濫砍濫伐、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情況”。B36依法律規(guī)定的意旨,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人,不限于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也可以是其他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成員,甚至還可以是城市居民。不過,在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中,還有兩個(gè)未明問題值得考慮:
第一,法條中所規(guī)定的“承包人死亡”,在承包人是個(gè)人的情況下,其含義無須爭(zhēng)議,但在由數(shù)人組成的農(nóng)戶為承包人的情況下,則可能有多種理解:其一,每一個(gè)戶內(nèi)成員死亡時(shí),其相應(yīng)的份額即可以由其繼承人繼承。其二,一個(gè)或部分成員死亡時(shí),由于農(nóng)戶仍然存在,應(yīng)由其他成員繼續(xù)承包,不發(fā)生繼承法上的繼承問題。只有當(dāng)承包農(nóng)戶中的成員全部死亡時(shí),才發(fā)生繼承問題。而當(dāng)承包人全部死亡時(shí),是每個(gè)成員的繼承人都有權(quán)主張繼承,還是只有該農(nóng)戶中最后一個(gè)死亡成員的繼承人可以繼承,則又有不同的認(rèn)識(shí)。對(duì)此問題,基于林地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以作為遺產(chǎn)來繼承的立法精神,筆者傾向于前一種理解。但如此理解,確實(shí)又存在與家庭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主體限制和功能定位是否吻合的問題。
第二,繼承人有多個(gè)時(shí),林地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如何具體分配?對(duì)此,筆者認(rèn)為,梁慧星教授主持?jǐn)M定的《中國(guó)物權(quán)法草案建議稿》第247條所提出的方案具有相當(dāng)合理性,可資參照,即:發(fā)生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繼承時(shí),繼承人不得將土地進(jìn)行登記上的分割,可以采取折價(jià)分割的方式;從事林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或?qū)儆谵r(nóng)業(yè)人口的繼承人,可以優(yōu)先分得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被繼承人的其他財(cái)產(chǎn)不足以與該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價(jià)值相當(dāng)時(shí),可采取折價(jià)補(bǔ)償?shù)姆绞秸移剑焕^承人均為非從事林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或者非農(nóng)業(yè)人口的,在繼承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后一年內(nèi),應(yīng)將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轉(zhuǎn)讓給從事林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者。
從立法論的角度看,筆者認(rèn)為,法律關(guān)于家庭承包的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例外地可以繼承的規(guī)定是否合理,不無疑問。因?yàn)槠渫瑯邮前凑杖巳擞蟹菰瓌t由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所進(jìn)行的承包,具有較強(qiáng)的身份性和社會(huì)保障功能,如果家庭承包獲得的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以繼承,則會(huì)造成林地的外流或繼承人獲得兩份承包地的結(jié)果,同樣背離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本旨和功能。且立法機(jī)關(guān)所述的例外允許林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作為遺產(chǎn)繼承的理由也并不充分(比如,同樣可能是投資大、收益慢的果園等特殊土地的承包,為何不能同樣地允許繼承?)因此,不如一律否定家庭承包下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以保持體系和立法精神上的一致性。
四、通過其他方式獲得的“四荒”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
由上文闡述和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定可知,對(duì)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四荒地”通過招標(biāo)、拍賣、公開協(xié)商等商業(yè)化方式而取得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財(cái)產(chǎn)屬性更為濃厚,B37其在權(quán)利的主體、客體、取得方式、承包期限、流轉(zhuǎn)方式等方面與家庭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顯有不同,幾乎不具有身份性,也不承載社會(huì)保障功能。因此,《土地承包法》第50條規(guī)定,“四荒地”的承包人死亡的,不僅其應(yīng)得的承包收益可以依照繼承法的規(guī)定繼承,其繼承人還可以在承包期內(nèi)繼續(xù)承包(即允許繼承)。B38而承包人的繼承人,既可以是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亦可以是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以外的人乃至非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城市居民。
唯需注意的是,由于“四荒地”的承包人是多元的(可以是一個(gè)人或數(shù)個(gè)人、家庭及法人或其他組織),因此,承包人死亡或消亡后所發(fā)生的法律后果也有不同。其中,以個(gè)人名義承包的情形居多,這種情況下在承包人死亡后,其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允許繼承,自不待言。B39 但在個(gè)別情況下,“其他方式的承包”中也存在以家庭為單位的承包,B40此種情況下是否允許繼承,尚有疑義。筆者認(rèn)為,此種承包不屬于前文論及的“家庭承包”,其并不負(fù)擔(dān)社會(huì)保障功能,作為家庭成員的承包人也不需要具有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的身份,因此每一名成員死亡后,其繼承人均可在承包期內(nèi)繼承其相應(yīng)份額的權(quán)益。由多個(gè)自然人共同承包的情況,亦同。在由企業(yè)或其他單位作為承包人而承包人在承包期內(nèi)消亡的情況下,其在剩余期限內(nèi)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及應(yīng)得的收益屬于企業(yè)或其他單位的財(cái)產(chǎn),應(yīng)由消亡單位權(quán)利義務(wù)的承受者接收,此不涉及繼承法上自然人死亡的遺產(chǎn)繼承問題。
雖然通過其他方式獲得的“四荒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可以繼承,但是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繼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在承包地的面積較小或繼承人較多時(shí),如果分別繼承承包地,則會(huì)造成土地的零碎化,不利于土地的利用效率。王漢斌同志在《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繼承法(草案)〉的說明》中也提到:“這種繼續(xù)承包不能按照遺產(chǎn)繼承的辦法。如果按照遺產(chǎn)繼承的辦法,那么同一順序的幾個(gè)繼承人,不管是否務(wù)農(nóng),不管是否有條件,都要均等承包,這對(duì)生產(chǎn)是不利的。”故此,有學(xué)者指出,為了防止“四荒地”使用權(quán)過分零碎而導(dǎo)致規(guī)模不經(jīng)濟(jì),當(dāng)有若干符合條件的繼承人時(shí),應(yīng)規(guī)定只能選擇其中一人或少數(shù)人繼承,而對(duì)其他繼承人的利益采取經(jīng)濟(jì)補(bǔ)償?shù)霓k法處理。B41這一主張與前述梁慧星教授主持?jǐn)M定的《中國(guó)物權(quán)法草案建議稿》第247條所提出的方案大致相當(dāng),可資采納。不過,當(dāng)承包地面積較大或分割后不會(huì)減損土地價(jià)值和利用效益時(shí),則無妨采用分割繼承的方式。
五、承包地征收補(bǔ)償費(fèi)的繼承問題
與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繼承相關(guān)的另一個(gè)問題是所承包土地被征收情況下的補(bǔ)償費(fèi)的繼承問題,即被繼承人在征地補(bǔ)償方案批準(zhǔn)之后,征地補(bǔ)償費(fèi)支付之前死亡的,其繼承人能否要求繼承征地補(bǔ)償費(fèi)?根據(jù)《物權(quán)法》第42條第2款、第132條和《土地管理法》第47條第2款的規(guī)定,征收土地的補(bǔ)償費(fèi)用包括土地補(bǔ)償費(fèi)、安置補(bǔ)助費(fèi)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bǔ)償費(fèi)等費(fèi)用。對(duì)于上列費(fèi)用得否繼承的問題,筆者認(rèn)為不應(yīng)一概而論。
土地補(bǔ)償費(fèi),是對(duì)集體土地所有權(quán)被征收的補(bǔ)償而不是對(duì)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補(bǔ)償,我國(guó)《土地管理法實(shí)施條例》第26條也明文規(guī)定土地補(bǔ)償費(fèi)歸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所有。因此,土地補(bǔ)償費(fèi)不屬于承包人的遺產(chǎn),其繼承人不得主張繼承。
安置補(bǔ)償費(fèi),源自原土地承包人的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是該項(xiàng)權(quán)益的變體。所以,筆者認(rèn)為其歸屬和在承包人部分或全部死亡時(shí)能否繼承的問題,應(yīng)依據(jù)前述與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同樣的規(guī)則處理:即在家庭承包的情況下,這些費(fèi)用同樣不能作為遺產(chǎn)而由繼承人繼承;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則可以繼承。
地上附著物和青苗歸承包人所有或?qū)儆诔邪说某邪找妫瑖?guó)務(wù)院《土地管理法實(shí)施條例》第26條第1款也規(guī)定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bǔ)償費(fèi)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在承包人死亡的情況下,這部分補(bǔ)償費(fèi)即轉(zhuǎn)變?yōu)樗勒叩倪z產(chǎn),當(dāng)然可以按照《繼承法》的規(guī)定繼承。唯需注意的是,當(dāng)家庭承包中的一個(gè)或部分成員死亡時(shí),由于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bǔ)償費(fèi)屬于家庭共有財(cái)產(chǎn),所以應(yīng)先進(jìn)行財(cái)產(chǎn)析分,只有死者的應(yīng)有份額部分才屬于遺產(chǎn)。
應(yīng)當(dāng)說明的是,我國(guó)已頒行的《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物權(quán)法》和目前正在進(jìn)行的繼承法的修訂,都是以當(dāng)時(shí)、當(dāng)下的國(guó)情和需要為基礎(chǔ)的。本文以上觀點(diǎn)也主要基于對(duì)現(xiàn)行法律和政策及現(xiàn)實(shí)國(guó)情的考量而從解釋論的角度進(jìn)行闡述。隨著我國(guó)農(nóng)村和整個(gè)社會(huì)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差異的消亡,從未來的立法論上考量,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未必永遠(yuǎn)不可自由流轉(zhuǎn)和繼承——當(dāng)我國(guó)未來的“農(nóng)民”不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職業(yè),基本社會(huì)保障制度惠及到每一位國(guó)民,各種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均不再具有身份性和社會(huì)保障功能而成為純粹的財(cái)產(chǎn)性權(quán)利的時(shí)候,它就自然可以作為遺產(chǎn),并可以由繼承人依照繼承法的規(guī)定繼承。
A Probe into Inheritance of the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Rural Land
LIU Bao-yu LI Yun-yang
Abstract:
1民法保護(hù)胎兒利益的理論基礎(chǔ)
1.1生命法益保護(hù)說
德國(guó)學(xué)者Planck認(rèn)為,胎兒利益雖非權(quán)利,但屬于生命法益,任何人均有權(quán)享有。因?yàn)樯ㄒ媸窍扔诜纱嬖冢巧泽w的本質(zhì),任何人對(duì)生命法益均有權(quán)享有,不受任何妨害或阻礙。任何人對(duì)人類自然生長(zhǎng)之妨礙或剝奪,均構(gòu)成對(duì)生命法益的侵害,胎兒利益受到侵害應(yīng)認(rèn)為是其內(nèi)部生命過程受到阻礙。
1.2權(quán)利能力說
持權(quán)利能力說的學(xué)者認(rèn)為,生命法益保護(hù)說對(duì)胎兒利益法律保護(hù)的理由訴諸于“自然”與“創(chuàng)造”末臻嚴(yán)謹(jǐn),因而致力于尋找實(shí)體法上的依據(jù)。如我國(guó)臺(tái)灣著名民法學(xué)者王澤鑒先生論述,“胎兒于未出生前,關(guān)于其個(gè)人的保護(hù)既已取得權(quán)利能力成為法律上的‘人’。故胎兒于出生前,就其身體健康(人身權(quán))所受侵害,得依法向加害人請(qǐng)求賠償為適當(dāng)、必要的治療,以恢復(fù)損害發(fā)生前之原狀。”[1]從這一論述可以看出王先生即認(rèn)為對(duì)胎兒利益予以保護(hù)的依據(jù)是胎兒具有一定的權(quán)利能力。
1.3人身權(quán)延伸保護(hù)說
該說認(rèn)為,人身權(quán)延伸保護(hù)的客體是胎兒的人身法益而非權(quán)利本身,因?yàn)榱⒎ㄕ卟怀姓J(rèn)其為權(quán)利,但承認(rèn)其為合法法益,并予以法律保護(hù),因而應(yīng)成為法律關(guān)系的客體。我國(guó)著名學(xué)者楊立新教授即認(rèn)為,法律在保護(hù)民事主體人身權(quán)的同時(shí),對(duì)于其在誕生前或死亡之后的人身法益,應(yīng)予以延伸的民法保護(hù)。[2]人身權(quán)延伸保護(hù)理論的基本思想是:在現(xiàn)代人權(quán)觀念的指導(dǎo)下,以維護(hù)自然人統(tǒng)一、完整的人身利益為基本目的,追求創(chuàng)造、保護(hù)社會(huì)利益與個(gè)人利益的和諧、統(tǒng)一。筆者認(rèn)為以上三種學(xué)說各有利弊。
針對(duì)生命法益說,其弊端在于它將胎兒利益的保護(hù)建立在自然和創(chuàng)造的抽象效力上,不是很有說服力,而且生命法益說沒有說明生命從何時(shí)開始,至何時(shí)結(jié)束;權(quán)利能力說無疑讓胎兒擁有了與自然人一樣的權(quán)利,包括生命權(quán)、名譽(yù)權(quán)、親權(quán)等人身權(quán)及物權(quán)、債權(quán)等財(cái)產(chǎn)權(quán)。但這一理論在賦予胎兒權(quán)利能力的同時(shí)也使得為胎兒設(shè)定義務(wù)成為可能。再者,這一理論亦無法解決我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中面臨的道德和法律難題,如我國(guó)實(shí)行多年的計(jì)劃生育政策是否侵犯了胎兒的生命權(quán),父母是否因墮胎失敗致胎兒出生而要承擔(dān)故意殺人未遂的刑責(zé)?
人身權(quán)延伸保護(hù)說,筆者認(rèn)為很有進(jìn)步意義,它認(rèn)為自然人在其出生前和死亡后,存在著與人身權(quán)利相聯(lián)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續(xù)人身法益,二者共同構(gòu)成了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突破了權(quán)利能力的限制與局限,很有借鑒意義,并且我國(guó)在著作權(quán)法上對(duì)作者死后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有法律規(guī)定,因此我們當(dāng)然可以對(duì)胎兒的利益做出相關(guān)規(guī)定,只不過一個(gè)是向前延伸,另一個(gè)是向后延伸而己。兩者都是生命兩端的自然延伸,都應(yīng)受到保護(hù)。然而其致命的弱點(diǎn)是沒有從根本上說明胎兒的利益為什么應(yīng)該受到保護(hù)。
2世界各國(guó)對(duì)胎兒利益保護(hù)的立法模式及我國(guó)法律保護(hù)的缺失
從目前世界各國(guó)的立法情況看,對(duì)胎兒賦予法律所擬定的主體資格,承認(rèn)胎兒具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已被越來越多的國(guó)家認(rèn)可和接受。與此相比,我國(guó)的立法明顯滯后,并且有很大的局限性。
2.1各國(guó)關(guān)于胎兒保護(hù)的立法模式
早在羅馬法時(shí)期,著名法學(xué)家保羅就提出:“當(dāng)涉及胎兒利益時(shí),母體中的胎兒像活人樣被對(duì)待,盡管在他出生以前這對(duì)他毫無裨益。”[3]這種法律精神已被有些國(guó)家和地區(qū)傳承至今,但立法的模式卻不盡相同。
1)概括保護(hù)主義概括保護(hù)主義,即胎兒出生時(shí)為活體的,溯及地取得民事權(quán)利能力。瑞士《民法典》第31條第2項(xiàng)規(guī)定:“子女,只要其出生時(shí)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權(quán)利能力。”原《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7條規(guī)定:“公民的權(quán)利能力在出生的時(shí)候發(fā)生,胎兒如果活著,也具有權(quán)利能力。”概括保護(hù)主義,因其對(duì)胎兒權(quán)益的保護(hù)相當(dāng)有力和和周延,符合民法保障人權(quán)的宗旨,也是司法實(shí)踐的需要,因而我國(guó)許多學(xué)者主張采納此種模式。但以權(quán)利能力為基點(diǎn)尋求胎兒利益的保護(hù)雖有優(yōu)越性,也暴露出不少矛盾。其一因?yàn)椤八^權(quán)利能力,不但指享有權(quán)利之能力而言,負(fù)擔(dān)義務(wù)之能力亦包含之”。[4]而對(duì)于胎兒來說,它只能享有民事權(quán)利,而不能承擔(dān)民事義務(wù),因此若對(duì)胎兒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一概加以確認(rèn),則有失公平,也不現(xiàn)實(shí);其二,這種立法例動(dòng)搖了傳統(tǒng)民法民事權(quán)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的信條,進(jìn)而可能引發(fā)一系列想像不到的問題,使整個(gè)法律內(nèi)部出現(xiàn)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也會(huì)隨之帶來更多的現(xiàn)實(shí)問題。
2)個(gè)別保護(hù)主義個(gè)別保護(hù)主義,也可稱為列舉式,認(rèn)為胎兒原則上無權(quán)利能力,僅對(duì)個(gè)別事例如對(duì)繼承、接受遺贈(zèng)、損害賠償請(qǐng)求等列明的事項(xiàng)具有權(quán)利能力,目前采用此例的國(guó)家主要有日、德、法等國(guó),這種立法例的優(yōu)點(diǎn)在于法律適用上的簡(jiǎn)單、明確,對(duì)于法律規(guī)定予以保護(hù)的,則加以保護(hù);反之,法律未作規(guī)定的,則不予考慮。如《法國(guó)民法典》第906條第1項(xiàng)規(guī)定:“為有受生前贈(zèng)與能力,以于贈(zèng)與時(shí)己受胎為己足”。第725條規(guī)定:“尚末受胎者,可得為繼承人。”第1923條規(guī)定:“在繼承開始時(shí)尚未出生,但己懷孕的胎兒,視為在繼承開始前出生。”《日本民法典》第721條規(guī)定:“胎兒,就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視為已出生。”在美國(guó),有關(guān)判例法規(guī)定,每一個(gè)人都被保護(hù),不受侵害之害,包括胎兒在內(nèi)。但個(gè)別保護(hù)主義很難達(dá)到以點(diǎn)覆面的效果,隨著社會(huì)的高速發(fā)展,涉及胎兒利益的保護(hù)事項(xiàng)必然趨于復(fù)雜,難以為立法者所事先預(yù)見。另外,條文的多寡,內(nèi)涵的大小,胎兒受保護(hù)利益的范圍,顯然很難窮盡對(duì)胎兒利益的羅列。
3)絕對(duì)否認(rèn)主義即絕對(duì)否認(rèn)胎兒具有權(quán)利能力。1964年《蘇俄民法典》第418條就采用此立法例。我國(guó)對(duì)胎兒利益的保護(hù)奉行的也是絕對(duì)否認(rèn)主義,這從我國(guó)《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中可以得到體現(xiàn)。此外,我國(guó)相關(guān)的婦女權(quán)益法中也有針對(duì)懷孕婦女權(quán)益保護(hù)等間接保護(hù)胎兒利益的規(guī)定,也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了我國(guó)目前采用的是絕對(duì)否認(rèn)主義,但是不難看出我國(guó)所采取的這種絕對(duì)否認(rèn)主義的立法例對(duì)胎兒利益的保護(hù)十分不利,很有局限性。在這種模式下,胎兒利益遭到侵害時(shí),尋求法律保護(hù)依據(jù)實(shí)屬難事。
2.2我國(guó)胎兒民事權(quán)利立法保護(hù)現(xiàn)狀和司法困局
1)我國(guó)胎兒民事權(quán)利保護(hù)的立法現(xiàn)狀目前,我國(guó)對(duì)胎兒的民事權(quán)利的立法保護(hù)主要體現(xiàn)在《繼承法》第28條中,該條規(guī)定:“遺產(chǎn)分割時(shí),應(yīng)當(dāng)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胎兒出生時(shí)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照法定繼承辦理”。這是我國(guó)現(xiàn)行法律可見的唯一直接保護(hù)胎兒利益的條文,但胎兒享有遺產(chǎn)權(quán)利卻必須從出生時(shí)開始,特留份留而不給,也很難保護(hù)胎兒的合法權(quán)益。盡管在《婦女權(quán)益保護(hù)法》也有間接保護(hù)胎兒利益的條文,但這些規(guī)定大多是站在保護(hù)孕婦利益的角度上,認(rèn)為保護(hù)了母親就是保護(hù)了胎兒,把對(duì)母親的保護(hù)認(rèn)為是對(duì)胎兒的保護(hù),這就混淆了保護(hù)母體和保護(hù)胎兒之間的關(guān)系。這是無法有效保護(hù)胎兒的權(quán)利和利益的,是種缺乏獨(dú)立性和完整性的保護(hù)。
2)我國(guó)法律關(guān)于自然人民事權(quán)利能力的規(guī)定所帶來的司法困局在司法實(shí)踐中,出生與否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是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的規(guī)定,“出生的時(shí)間以戶籍證明為準(zhǔn);沒有戶籍證明的,以醫(yī)院出具的出生證明為準(zhǔn);沒有醫(yī)院證明的,參照其他有關(guān)證明認(rèn)定。”權(quán)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時(shí)間以戶籍登記或醫(yī)院出生證為準(zhǔn),從而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與實(shí)際出生不一致,使實(shí)際上己經(jīng)出生但由于某種原因沒有及時(shí)進(jìn)行戶籍登記或取得出生證的孩子在此期間的合法權(quán)益得不到法律保護(hù);另一方面,若胎兒在出生前、出生過程中,或者出生后辦理戶籍登記或者出生證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間接損害,也必然會(huì)因權(quán)利能力障礙而不能以權(quán)利主體的身份獲得法律保護(hù)。在轟動(dòng)一時(shí)的我國(guó)首例對(duì)“胎兒”的人身權(quán)利予以法律保護(hù)的案例中,胎兒“小石頭”在分娩前的胎兒期,受到醫(yī)生產(chǎn)鉗傷害,為他以后的人生帶來了損害后果,既然助產(chǎn)行為與“小石頭”受損害之間有因果關(guān)系,他就完全有權(quán)利請(qǐng)求損害賠償,并且只有“小石頭”作為原告提訟,他的合法權(quán)利才能得到更有效的保護(hù),他受到的傷害才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補(bǔ)償。[5]雖然這一案例因首次保護(hù)了胎兒的的權(quán)益而為世人所稱道,但卻因囿于法律規(guī)定的限制未能更好的保護(hù)受害人的利益而令人遺憾,更合理的狀態(tài)是:就“小石頭”的利益保護(hù)而言,應(yīng)由“小石頭”直接以其自己的名義,因?yàn)槭軅Φ氖恰靶∈^”本人,而要求損害賠償?shù)囊矐?yīng)該是他本人,醫(yī)院不但要對(duì)“小石頭”人身受到的直接損害進(jìn)行賠償,還應(yīng)對(duì)其所受精神上的傷害進(jìn)行賠償,當(dāng)然,這樣做并不否認(rèn)其母親因此事受傷害而要求損害賠償?shù)臋?quán)利。
3關(guān)于胎兒利益保護(hù)的立法建議
3.1賦予胎兒特殊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
1)應(yīng)該賦予胎兒民事權(quán)利能力胎兒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是指胎兒依法享有民事權(quán)利和承擔(dān)民事義務(wù)的資格,這是確立胎兒民事主體地位的法律基礎(chǔ)。我國(guó)《民法通則》規(guī)定自然人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始于出生,由于胎兒尚未出生,不具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不是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主體。但是,每個(gè)民事主體都要經(jīng)歷從受孕到出生的過程。在這個(gè)過程中,不僅胎兒的某些實(shí)際利益需要保護(hù),而且某些未來的利益也需要得到有效保護(hù)。因此,“只因出生時(shí)間的純粹偶然性而否定其權(quán)利是不公平的”。[6]梁慧星在《中國(guó)民法典:總則編條文建議稿》中指出:“凡涉及胎兒利益保護(hù)的,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王澤鑒老師在點(diǎn)評(píng)1955年臺(tái)上字第943號(hào)判決時(shí)指出:“依吾人見解,......,故胎兒雖未出生,已享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可見,學(xué)界有些學(xué)者對(duì)賦予胎兒民事權(quán)利能力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
2)胎兒所享有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應(yīng)當(dāng)具有其特殊性胎兒雖然具有生理上的完整性,是自然人成為民事主體的初始階段,但胎兒與自然人畢竟還是有一定區(qū)別的:自然人是已經(jīng)出生的人,而懷孕期間的胎兒尚未出生。由于胎兒尚未出生,不具有民事行為能力,不具備承擔(dān)民事義務(wù)的條件;此外,胎兒也無法把進(jìn)行某一民事行為的內(nèi)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達(dá)于外部,即不能進(jìn)行相應(yīng)的意思表示。因此賦予胎兒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應(yīng)當(dāng)具有特殊性,即不附加義務(wù)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
3.2胎兒享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的時(shí)間應(yīng)當(dāng)從受孕時(shí)開始
羅馬法認(rèn)為,胎兒從現(xiàn)實(shí)角度上講不是人,但由于他仍然是一個(gè)潛在的人,人們?yōu)樗4娌⒕S護(hù)自出生之時(shí)起即歸其所有的那些權(quán)利,這種權(quán)利能力自受孕之時(shí)起而不是從出生之時(shí)起計(jì)算。從醫(yī)學(xué)的角度來看,自然人自受孕至出生這一期間為生命完整的孕育過程。受孕是胎兒開始存在的標(biāo)志,也是胎兒的原始狀態(tài),只有經(jīng)過受孕階段,胎兒才能成形,具備生理上的人的完整性;只有經(jīng)過受孕階段,胎兒才有成為民事意義上的人的可能性,為出生后順利成為真止意義上的自然人作好準(zhǔn)備。因此,從受孕時(shí)起賦予胎兒民事權(quán)利能力是正確的,是絕對(duì)必要的,而且隨著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的發(fā)展,胎兒正常發(fā)育并存活的可能性大增,故而做這樣的制度設(shè)計(jì)也有其現(xiàn)實(shí)性。
3.3胎兒出生時(shí)為死體的,其民事權(quán)利能力視為自始不存在
胎兒雖然是人的初始階段,但畢竟不是現(xiàn)行法意義上的人,保護(hù)胎兒的利益實(shí)際上保護(hù)的是一種期待權(quán),該期待權(quán)轉(zhuǎn)化為既得權(quán)的條件就是胎兒活著出生。當(dāng)胎兒出生時(shí)為死體的,如果仍然承認(rèn)其出生前具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在法理上是說不通的。德國(guó)法的理論、立法和司法實(shí)踐都確定了這樣一個(gè)基本原則:胎兒在母體中受到侵權(quán)行為的侵害,身體、健康受到損害,有權(quán)在其出生后就其損害請(qǐng)求損害賠償。可見,西方一些國(guó)家也認(rèn)為胎兒民事權(quán)利能力在出生時(shí)為死體時(shí)其權(quán)利能力溯及地取消,對(duì)胎兒利益的保護(hù)以出生時(shí)為活體作為先決條件。當(dāng)然如果是在胎兒因他人侵權(quán)而意外流產(chǎn)或者出生后為死體的情況下,仍有一個(gè)胎兒利益的保護(hù)問題,只不過此時(shí)的保護(hù)只能以對(duì)母親利益的保護(hù)而間接實(shí)現(xiàn),或者說此時(shí)更關(guān)注的是母親利益的保護(hù)問題。
3.4母體在懷孕期間遭受不法侵害,胎兒出生時(shí)為活體的,損害賠償清求權(quán)的訴訟時(shí)效期間
1)母體在懷孕期間遭受不法侵害,該損害在胎兒出生后比較明顯的,比如胎兒畸形、生而殘障等。由于在這種情況下,損害結(jié)果已經(jīng)發(fā)生,認(rèn)定較為容易;加之胎兒急需要進(jìn)行相應(yīng)的救治,此時(shí)損害賠償清求權(quán)可以由其法定人或者監(jiān)護(hù)人代為行使訴訟時(shí)效適用《民法通則》第136條第1款的規(guī)定:“身體受到傷害要求賠償?shù)模V訟時(shí)效期間為一年”,該期間的起算從胎兒出生的第二天算起。
2)母體在懷孕期間遭受不法侵害,胎兒出生后該損害沒有即刻表現(xiàn)出來,而是經(jīng)過較長(zhǎng)時(shí)間才能顯現(xiàn),即隱形的、不明顯的損害,比如毒性尚未發(fā)作、胎兒發(fā)育遲緩、表達(dá)障礙等。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賦予胎兒20年的最長(zhǎng)訴訟時(shí)效。因?yàn)樘撼錾鷷r(shí)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能真實(shí)地表達(dá)自己的意愿,包括自己的受損害的狀況及行使損害賠償清求權(quán)等。胎兒所遭受的損害只有胎兒自己才能真正地感知,但是這種感知是要具備相應(yīng)的民事行為能力的,這種民事行為能力應(yīng)該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只有賦予胎兒最長(zhǎng)的訴訟時(shí)效期間,為胎兒利益的保護(hù)留下足夠的時(shí)間空間,直到其成長(zhǎng)為具有民法意義上的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才能更好地保護(hù)胎兒的權(quán)利。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歐盟及其前身(歐共體)頒布了一系列指令,從而催生了具有統(tǒng)一性(至少具有協(xié)調(diào)性)的歐洲民法。就侵權(quán)法而言,《關(guān)于產(chǎn)品責(zé)任的指令》已在14個(gè)歐盟成員國(guó)中得以執(zhí)行,并影響到了歐洲之外國(guó)家的民事立法:就合同法而言,《關(guān)于消費(fèi)者合同中不公平條款的指令》覆蓋了合同法的核心部分,并已經(jīng)在絕大多數(shù)成員國(guó)中得到實(shí)施。目前歐洲的學(xué)者們還在討論《關(guān)于消費(fèi)品的銷售及其相關(guān)擔(dān)保問題的指令》的草案。
當(dāng)然,協(xié)調(diào)民法領(lǐng)域中的侵權(quán)法、合同法問題并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例如《關(guān)于產(chǎn)品責(zé)任的指令》的合憲性就曾受到政治家們的詰難;而《關(guān)于服務(wù)領(lǐng)域責(zé)任問題的指令》的草案則遭到了來自于學(xué)術(shù)界、生產(chǎn)商和消費(fèi)者等各個(gè)方面的攻擊。這就引發(fā)了下述幾個(gè)問題:是否有必要制定《歐洲民法典》;根據(jù)《羅馬條約》、《馬斯特利赫條約》及《阿姆斯特丹條約》制定《歐洲民法典》是否具有憲法基礎(chǔ);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話,如何制定《歐洲民法典》?是按照大陸法系還是按照普通法系的體例制定,是否應(yīng)當(dāng)同時(shí)規(guī)定民法總則和民法分則,如物權(quán)法、合同法和侵權(quán)法?為探討這些問題,作為歐盟主席國(guó)的荷蘭司法部于1997 年2月28日,在荷蘭海牙附近的申維根市(scheveningen)召開了為期一天的關(guān)于制定《歐洲民法典》可行性的研討會(huì)。許多私法專家向會(huì)議提交了論文,并就起草《歐洲民法典》的法律基礎(chǔ)、存在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希臘海倫尼克國(guó)際與外國(guó)法研究所的克萊默斯(kerameus)教授還探討了起草《歐洲民法典》的班子問題,荷蘭最高法院的副院長(zhǎng)施耐德博士更是明確主張建立一個(gè)常設(shè)機(jī)構(gòu)。本文擬就該次會(huì)議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做一述評(píng)。
二、制定《歐洲民法典》的必要性及法律基礎(chǔ)
歐洲議會(huì)曾三次作出一致建議,批準(zhǔn)《歐洲民法典》的起草研究項(xiàng)目。這并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在于歐洲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浪潮中,歐盟成員國(guó)民法規(guī)范的不統(tǒng)一容易造成新型的法律歧視。也就是說,歐洲統(tǒng)一大市場(chǎng)中民事主體在同一情形下由于成員國(guó)民法的不同規(guī)定享受不同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為了確保歐洲統(tǒng)一大市場(chǎng)的公平和效率,必須采取切實(shí)有效措施實(shí)現(xiàn)歐盟法律的有機(jī)性。而歐盟法律的有機(jī)性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gè)層次:一是歐盟規(guī)則之間的連貫性(例如關(guān)于侵權(quán)責(zé)任的兩套歐盟法律規(guī)則就需要?dú)W洲法院予以協(xié)調(diào));二是歐盟成員國(guó)規(guī)則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性,這種協(xié)調(diào)主要是通過歐盟的指令,如產(chǎn)品責(zé)任指令;三是各個(gè)歐盟成員國(guó)內(nèi)部規(guī)則之間的同質(zhì)性。就確保各歐盟成員國(guó)內(nèi)部規(guī)則之間的同質(zhì)性而言,也有許多問題需要予以解決。例如,公司與消費(fèi)者訂立了不公平合同條款受《關(guān)于消費(fèi)者合同中不公平條款的指令》影響下的國(guó)內(nèi)法規(guī)則的調(diào)整,而公司與其他當(dāng)事人訂立的不公平合同條款卻不必受該指令的影響和調(diào)整,這就產(chǎn)生了具有同一性質(zhì)的民事關(guān)系卻適用不同國(guó)內(nèi)法規(guī)則的問題。
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起草《歐洲民法典》的設(shè)想應(yīng)當(dāng)是一個(gè)立法協(xié)調(diào)項(xiàng)目,這也符合《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00條及100條甲之規(guī)定。事實(shí)上,歐洲議會(huì)曾要求委員會(huì)著手起草《歐洲民法典》,委員會(huì)也沒有拒絕,只不過沒有迅速采取行動(dòng)而已。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起草《歐洲民法典》主要是一個(gè)學(xué)術(shù)意義上的研究課題。當(dāng)然,從學(xué)術(shù)研究的角度探討起草《歐洲民法典》問題也很有必要。歐洲,特別是西部歐洲的變化日新月異,一些新的法律問題經(jīng)常出現(xiàn)。(1)有些問題,例如大氣污染、 空中交通管制、風(fēng)險(xiǎn)投資控制和難民的管理等問題不可能在一國(guó)之內(nèi)得到解決。(2)對(duì)于有些新問題,國(guó)內(nèi)現(xiàn)行立法缺乏明確規(guī)定。例如, 勞動(dòng)法和社會(huì)保障法中的平等原則的實(shí)施、新醫(yī)藥產(chǎn)品未知風(fēng)險(xiǎn)的責(zé)任、水質(zhì)或土壤污染的責(zé)任、家庭法和人權(quán)保護(hù)法的關(guān)系等問題都是如此。律師們對(duì)于上述這兩類問題往往無法從一國(guó)的法典、成文法和現(xiàn)存判例中尋求答案,只能借助比較法方法。例如,英國(guó)上議院在審理設(shè)計(jì)律師責(zé)任的懷特訴約翰一案時(shí),直接從德國(guó)法中尋找判案依據(jù),而未作任何進(jìn)一步的說明。從這一角度來說,起草《歐洲民法典》對(duì)于解決這些新興的民事法律問題確有裨益。
當(dāng)然,也有學(xué)者反對(duì)制定《歐洲民法典》,認(rèn)為很難找到制定《歐洲民法典》的法律依據(jù);至于《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00條及100條甲之規(guī)定雖然可以作為消費(fèi)者保護(hù)立法協(xié)調(diào)的法律基礎(chǔ),但不宜作為制定歐洲債法乃至于《歐洲民法典》的法律基礎(chǔ)。此外,從目前的政治氣氛來看,歐盟正全力以赴準(zhǔn)備經(jīng)濟(jì)和貨幣聯(lián)盟,擴(kuò)大申根協(xié)議加入國(guó)、吸納3個(gè)中歐國(guó)家加入歐盟等一系列計(jì)劃上, 尚無暇問及制定《歐洲民法典》這一長(zhǎng)期工程。荷蘭的新民法典半個(gè)世紀(jì)以前就已著手制定,然而直至今日還未完全竣工,因此制定一部《歐洲民法典》同樣是一項(xiàng)曠日持久的事業(yè),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此外,法律是一國(guó)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因此應(yīng)該維護(hù)各國(guó)法律的特色。反對(duì)者認(rèn)為,沒有一個(gè)象國(guó)家立法機(jī)關(guān)那樣的歐盟立法機(jī)關(guān),有能力統(tǒng)一調(diào)整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保持民法中民族和地區(qū)的差異性非常有必要,既要維護(hù)文化的差異性,也要維護(hù)法律的差異性。私法是一國(guó)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應(yīng)該保留國(guó)內(nèi)法,由國(guó)家議會(huì)來改變或保持不變。因此,要實(shí)現(xiàn)歐盟法與國(guó)內(nèi)法之間的協(xié)調(diào)勢(shì)必比登天還難。而且,如果絕大多數(shù)歐盟成員已經(jīng)采納國(guó)際私法中的實(shí)體規(guī)范,就沒必要再制定歐洲層次上的民法典。
但是,客觀說來制定《歐洲民法典》有利于實(shí)現(xiàn)歐盟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基本規(guī)則與歐盟經(jīng)濟(jì)一體化步伐的協(xié)調(diào),降低歐盟范圍內(nèi)民事流轉(zhuǎn)的交易成本,其積極作用顯而易見。因此,一個(gè)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制定《歐洲民法典》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據(jù)。
贊成制定《歐洲民法典》的歐洲學(xué)者往往從《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00條及第100條甲第1款尋求法律基礎(chǔ)。《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00條規(guī)定,“經(jīng)委員會(huì)建議并同歐洲議會(huì)及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委員會(huì)協(xié)商后,理事會(huì)應(yīng)以一致同意發(fā)出指令,以使各成員國(guó)對(duì)共同市場(chǎng)的建立和運(yùn)轉(zhuǎn)發(fā)生直接影響的法律、 條例或行政法規(guī)趨于一致。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00條甲第1款規(guī)定,“理事會(huì)應(yīng)依據(jù)第189 條乙中的程序并同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委員會(huì)協(xié)商后,采取措施以使那些以內(nèi)部市場(chǎng)的建立和運(yùn)轉(zhuǎn)作為其目標(biāo)的成員國(guó)的法律、條例或行政法規(guī)趨于一致。”
洛文天主教大學(xué)經(jīng)濟(jì)法系教授格爾文(gereven)認(rèn)為,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00條比起第100條甲第1款來,適用范圍要廣。 只要成員國(guó)立法直接影響到共同市場(chǎng)的建立和運(yùn)轉(zhuǎn),即屬前者協(xié)調(diào)之列;而后者協(xié)調(diào)的范圍只限于旨在推動(dòng)成員國(guó)內(nèi)部市場(chǎng)的建立和運(yùn)轉(zhuǎn)的國(guó)內(nèi)立法。第100條甲調(diào)整的對(duì)象主要是成員國(guó)內(nèi)部市場(chǎng), 而不是歐洲整個(gè)大市場(chǎng)。依據(jù)該條予以協(xié)調(diào)的成員國(guó)民法僅限于各國(guó)民法典中有關(guān)反對(duì)企業(yè)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的條款和保護(hù)消費(fèi)者條款。就物權(quán)法、合同法、侵權(quán)法而言,很難說其唯一目標(biāo)在于推動(dòng)成員國(guó)內(nèi)部市場(chǎng)的建立和運(yùn)轉(zhuǎn),但可以被視為直接影響到共同市場(chǎng)的建立和運(yùn)轉(zhuǎn)。
他認(rèn)為,即使《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00條與第100條甲各有不足,前者在立法協(xié)調(diào)的程序上靈活性不強(qiáng)(理事會(huì)決議采取理事會(huì)成員一致表決主義),后者在立法協(xié)調(diào)的法律基礎(chǔ)上不夠廣泛;仍然可以在該條約第235條找到制定《歐洲民法典》的基礎(chǔ)。
而德國(guó)海德堡大學(xué)的教授鐵爾曼(tilmann)則認(rèn)為, 只有《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00甲才能成為制定《歐洲民法典》的基礎(chǔ)。因?yàn)椋?該條的優(yōu)點(diǎn)在于:歐盟立法機(jī)關(guān)在進(jìn)行立法協(xié)調(diào)時(shí)采取多數(shù)決定原則,而非一致決定原則;歐洲議會(huì)能夠發(fā)揮影響;立法協(xié)調(diào)的手段既包括指令,也包括規(guī)章;歐洲法院還可就立法協(xié)調(diào)作出司法解釋。
折衷性觀點(diǎn)則認(rèn)為:一方面,成員國(guó)不應(yīng)該被迫編纂其私法,甚至在歐盟層次進(jìn)行私法協(xié)調(diào);另一方面,歐洲的非歐盟成員國(guó)應(yīng)當(dāng)被允許參與起草《歐洲民法典》的進(jìn)程。
三、《歐洲民法典》調(diào)整對(duì)象問題
關(guān)于《歐洲民法典》調(diào)整對(duì)象,歐洲民法學(xué)家的意見比較一致。認(rèn)為,歐盟主要是一個(gè)經(jīng)濟(jì)意義上的聯(lián)盟,建立歐洲統(tǒng)一大市場(chǎng)的目的決定了《歐洲民法典》只應(yīng)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而不調(diào)整人身關(guān)系。相應(yīng)地,《歐洲民法典》主要包括物權(quán)法、合同法和侵權(quán)法;至于人法、親屬法和繼承法則應(yīng)由成員國(guó)的國(guó)內(nèi)法予以調(diào)整。一項(xiàng)關(guān)于繼受外國(guó)法難易程度的調(diào)查表明,人們比較容易接受有關(guān)合同、侵權(quán)、公司、勞動(dòng)關(guān)系和租售協(xié)議等方面的新法律規(guī)則,但很難接受婚姻、繼承和對(duì)未成年人監(jiān)護(hù)權(quán)等方面法律規(guī)則的變遷。這除了社會(huì)行為模式的影響之外,還有宗教和道德的因素。當(dāng)然,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社會(huì)化歐洲的整合、歐盟成員國(guó)之間文化和社會(huì)行為模式的融合,逐漸把人身關(guān)系納入《歐洲民法典》也是可能的。
就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而言,《歐洲民法典》的調(diào)整范圍應(yīng)當(dāng)寬一些,還是應(yīng)當(dāng)窄一些,也很有爭(zhēng)議。突出表現(xiàn)在,《歐洲民法典》的調(diào)整范圍應(yīng)當(dāng)局限于歐盟內(nèi)部的跨國(guó)性民事關(guān)系,還是同時(shí)包括純粹的國(guó)內(nèi)民事關(guān)系這一問題上。按照后一思路,不必劃分歐盟內(nèi)部的國(guó)際民事關(guān)系與國(guó)內(nèi)民事關(guān)系,似乎合于歐洲精神。但其難度可以想見,不如前一思路可行:(1)根據(jù)《歐共體條約》第3條乙第2段確定的從屬性原則, 按照后一思路制定《歐洲民法典》不屬于歐盟的專屬權(quán)限范圍,而按照前一思路制定《歐洲民法典》則屬于歐盟的專屬權(quán)限范圍;(2 )制定《歐洲民法典》的主要原因在于調(diào)整歐盟內(nèi)部跨國(guó)性民事關(guān)系的必要性,至于純粹的國(guó)內(nèi)民事關(guān)系則應(yīng)適用各國(guó)的不同民法制度;(3 )絕大多數(shù)成員國(guó)把法律制度視為本國(guó)文化精粹中的一部分,保留其國(guó)內(nèi)民法的愿望十分強(qiáng)烈,在主要法系國(guó)家(如英國(guó)、法國(guó)和德國(guó))尤為根深蒂固。因此,《歐洲民法典》的總則和分則必須圍繞歐盟內(nèi)部的國(guó)際民事關(guān)系予以設(shè)計(jì)。否則,只能是烏托邦式的空想,最終無法實(shí)現(xiàn)。
當(dāng)然,也有學(xué)者提出反對(duì)意見。理由之一是,擔(dān)心上述思路會(huì)導(dǎo)致關(guān)于歐洲合同法范圍的無止境的爭(zhēng)論。例如,德國(guó)與匈牙利之間的合同關(guān)系是否具有歐盟內(nèi)部的國(guó)際民事關(guān)系特點(diǎn);如果英國(guó)不加入《歐洲民法典》,荷蘭與英國(guó)之間的合同關(guān)系是否具有歐盟內(nèi)部的國(guó)際民事關(guān)系特點(diǎn);同一國(guó)家的兩個(gè)商人締結(jié)的買賣關(guān)系中,如果貨物在第二國(guó),運(yùn)輸目的地在第三國(guó),此種買賣關(guān)系是否具有歐盟內(nèi)部的國(guó)際民事關(guān)系特點(diǎn)?理由之二是,起草《歐洲民法典》之初就限制調(diào)整范圍,無疑是對(duì)起草者的熱情潑涼水。
誠(chéng)然,從法學(xué)家的理想來看,除了受本國(guó)文化影響較重、很難統(tǒng)一,或者從性質(zhì)上看無法統(tǒng)一的民事關(guān)系,都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地納入《歐洲民法典》的調(diào)整范圍。這樣,統(tǒng)一的民事法律規(guī)范越多,私法沖突的可能性就越小,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確定性就越有所保障。但是,從務(wù)實(shí)的角度出發(fā),我贊同第一種意見。當(dāng)然,《歐洲民法典》的調(diào)整范圍局限于歐盟內(nèi)部的跨國(guó)性民事關(guān)系,并不妨礙國(guó)內(nèi)民事關(guān)系的當(dāng)事人根據(jù)私法自治原則選擇適用《歐洲民法典》,也不妨礙歐盟成員國(guó)以《歐洲民法典》為樣板法修改其國(guó)內(nèi)民法,或者通過特別法律直接規(guī)定國(guó)內(nèi)民事關(guān)系參照適用《歐洲民法典》。
談到《歐洲民法典》調(diào)整對(duì)象,不能不觸及民商合一主義與民商分立主義的選擇問題。以卓布尼格(drobnig)為代表的通說認(rèn)為, 應(yīng)當(dāng)效法1992年《荷蘭民法典》和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對(duì)《歐洲民法典》實(shí)行民商合一主義。他還認(rèn)為,民法與商法的區(qū)別正在慢慢地被消費(fèi)者法與非消費(fèi)者法所取代,現(xiàn)行的歐洲消費(fèi)者合同立法就強(qiáng)調(diào)這種劃分。
四、《歐洲民法典》的結(jié)構(gòu)
《歐洲民法典》的結(jié)構(gòu)也是歐洲學(xué)者探討的一個(gè)主要問題。《歐洲民法典》應(yīng)否規(guī)定總則,就很有爭(zhēng)議。德國(guó)馬普研究所的卓布尼格教授持肯定說,理由有四:(1)總則條款有利于統(tǒng)領(lǐng)分則條款, 確保民法典的和諧性;(2)總則條款有利于減少分則條款, 從而加快立法步伐;(3 )總則條款有利于民法典本身在新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情勢(shì)面前作出必要的自我調(diào)整;(4)總則條款有利于促進(jìn)對(duì)法律的教學(xué)與理解, 從而提高法律的實(shí)施效率。而法國(guó)的塔侖教授則持否定說。這當(dāng)然與各國(guó)不同的民法傳統(tǒng)有關(guān),比如《德國(guó)民法典》包括總則,而《法國(guó)民法典》則并不包括總則。按照卓布尼格的設(shè)想,《歐洲民法典》的總則分為兩部分:(1)一般原則。包括適用范圍, 一般原則(《歐洲民法典》權(quán)利:人身自由,反對(duì)歧視;結(jié)社權(quán);財(cái)產(chǎn));其他法律淵源,法典的解釋。(2)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法的基本原則:法律行為;的權(quán)限;物與權(quán)利;金錢債權(quán);信義關(guān)系(或者信托關(guān)系);履行;不履行;抵銷;責(zé)任;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的多元性;術(shù)語的含義與時(shí)效期間。
關(guān)于債法與合同法。一般債法是各國(guó)民法中最抽象的部分。第一屆至第三屆蘭多委員會(huì)一直把一般債法作為歐洲民法典的調(diào)整對(duì)象。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的合同關(guān)系要遵循契約自由原則。因此有關(guān)合同成立與履行的法律規(guī)則必須合乎一定的邏輯要求和交易活動(dòng)的要求。合同法與家庭法、繼承法不同,具有較強(qiáng)的技術(shù)性,很少受民族傳統(tǒng)和社會(huì)信仰的影響。因此,在《歐洲民法典》中詳細(xì)規(guī)定債法和合同法遇到的阻力較小。鑒于合同法的重要性,由學(xué)者主張以合同法作為《歐洲民法典》的開篇。但是,該觀點(diǎn)遭到了批評(píng)。伯奈爾教授認(rèn)為,法典的第一部分應(yīng)該是總則性條款,而不應(yīng)是具體的分則條款。有學(xué)者提議,作為一部體系化的法典,《歐洲民法典》中的債法不僅應(yīng)包括合同法和侵權(quán)法等內(nèi)容,還應(yīng)囊括返還法、不當(dāng)?shù)美c“準(zhǔn)合同”。
關(guān)于物權(quán)法。物權(quán)法與侵權(quán)法、合同法共同構(gòu)成了傳統(tǒng)民法體系中的三大支柱。卓布尼格主張,物權(quán)部分的重心在于動(dòng)產(chǎn)物權(quán);至于不動(dòng)產(chǎn)物權(quán)中的抵押權(quán)也可納入該部分。米蘭大學(xué)的佳姆巴洛認(rèn)為,歐洲大多數(shù)民法典中的物權(quán)法具有極強(qiáng)的本土性,有著數(shù)百年的本國(guó)法律傳統(tǒng)。因此,要在《歐洲民法典》中納入完備的物權(quán)制度,必須對(duì)各國(guó)的物權(quán)法進(jìn)行合理的揚(yáng)棄。但究竟應(yīng)當(dāng)拋棄哪些國(guó)家的哪些物權(quán)法制度,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下結(jié)論的。總的原則是,既要盡可能尊重大多數(shù)國(guó)家的物權(quán)法傳統(tǒng),照顧不同國(guó)家物權(quán)法的個(gè)性,也要充分保護(hù)物的流通和經(jīng)濟(jì)效用,謀求最大限度的共同物權(quán)法規(guī)則。
關(guān)于《歐洲民法典》抽象性與具體性的把握。《歐洲民法典》的條款應(yīng)當(dāng)原則些,還是應(yīng)當(dāng)具體些,也是一個(gè)頗有爭(zhēng)議的話題。學(xué)者們傾向于最好既不采取高度抽象化,因而適用范圍受到嚴(yán)格限制的模式,也不采取非常技術(shù)化、具體化的模式,而應(yīng)當(dāng)實(shí)現(xiàn)兩者的有機(jī)結(jié)合。《荷蘭民法典》第3編就提供了一種很好的范例。一般說來, 歐盟成員國(guó)之間比較容易就具體的法律制度達(dá)成妥協(xié),但就抽象的法律原則或者抽象程度更高一級(jí)的法律規(guī)則達(dá)成妥協(xié)就要難一些。因此,《歐洲民法典》的條款越具體越容易減少阻力,易于被接受。但是,只有具體條款孤軍深入,而沒有適度抽象的法律條款作指南,也會(huì)影響《歐洲民法典》應(yīng)有作用的發(fā)揮。
五、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區(qū)分對(duì)制定《歐洲民法典》的影響
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劃分并不是不可調(diào)和的。普通法和大陸法國(guó)家共同參加歐盟的立法活動(dòng),共同制定《聯(lián)合國(guó)貨物銷售公約》,共同參加海牙國(guó)際私法會(huì)議的工作等,都是明顯的例證。歐盟范圍內(nèi)就民法中的嶄新而重要的問題而制定的《產(chǎn)品責(zé)任指令》,以及世界范圍內(nèi)比較成功的《聯(lián)合國(guó)貨物銷售公約》都是不同法系互相調(diào)整的產(chǎn)物。當(dāng)然,歐盟立法在協(xié)調(diào)兩大法系方面往往僅涉及商標(biāo)、產(chǎn)品責(zé)任等具體的民法問題,很少涉及一般民法制度或者債法。戈?duì)栁暮蛶炱章颊J(rèn)為,歐盟這種零敲碎打的立法思路帶有不少缺陷,必須制定出體系化的民法典,以統(tǒng)帥和整合各項(xiàng)零散的民事立法協(xié)調(diào)措施。
目前歐洲學(xué)者的通說認(rèn)為,普通法系民法和大陸法系民法的區(qū)分并不象比較法著作30年之前所認(rèn)為的那樣絕對(duì)。第一,普通法系中的民事立法數(shù)量已大幅增長(zhǎng)。諸如消費(fèi)者、承租人、雇員、未成年人、外國(guó)雇員、女職工的保護(hù)問題都已由立法予以調(diào)整。第二,大陸法系中判例法的重要性也日益明顯,私法領(lǐng)域中的許多方面已接受判例法的調(diào)整,在侵權(quán)法領(lǐng)域內(nèi)尤為突出。例如,在法國(guó)、荷蘭、比利時(shí)和盧森堡,民法典對(duì)于侵權(quán)行為的規(guī)定十分簡(jiǎn)單、原則。但是,法院判例在這些簡(jiǎn)單規(guī)定的基礎(chǔ)上,就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國(guó)家責(zé)任、醫(yī)療事故責(zé)任和交通事故責(zé)任等問題,提出了一整套具體的適用標(biāo)準(zhǔn)。后來案件的判決都以先前案件的判決為基礎(chǔ)。這種兩大法系相互融合的趨勢(shì)在合同法和侵權(quán)法領(lǐng)域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而在物權(quán)法領(lǐng)域,特別是不動(dòng)產(chǎn)物權(quán)和抵押權(quán)方面,則進(jìn)展緩慢。第三,歐洲法院創(chuàng)設(shè)法律基本原則的方式的影響日益增大。例如,歐洲人權(quán)法院根據(jù)《歐洲保護(hù)人權(quán)與基本自由的公約》中的模糊條款發(fā)展了一套原則以保護(hù)人權(quán)和基本的自由。類似地歐洲法院在借鑒成員國(guó)立法規(guī)定的基礎(chǔ)上,也提出了一系列適用于歐盟法領(lǐng)域的基本法律原則,并為成員國(guó)法院所采納。其中的合乎比例原則,就被英國(guó)法院所接受,盡管該原則對(duì)于英國(guó)法院來說是聞所未聞的。第四,諸多國(guó)際商事公約的問世是兩大法系互相融合、彼此寬容的又一個(gè)重要趨勢(shì)。例如,1980年的《聯(lián)合國(guó)貨物銷售公約》已經(jīng)在50個(gè)國(guó)家被批準(zhǔn),40個(gè)是大陸法系國(guó)家,10個(gè)是普通法系的國(guó)家,即是明證。因此,雖然兩大法系的區(qū)分會(huì)在法律原則、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上給《歐洲民法典》的制定帶來不少困難,但這并不必然成為制定《歐洲民法典》的障礙。
六、《歐洲民法典》應(yīng)該采取的形式
制定《歐洲民法典》是采取由單獨(dú)條約所確定的統(tǒng)一法形式,還是采取樣板法形式,也頗值探討。如果采取樣板法,有些歐盟成員國(guó)(例如英國(guó))就得把《歐洲民法典》拒之門外,而感興趣的一些非歐盟成員國(guó)(例如挪威、匈牙利、塞浦路斯)則可以自由地采用《歐洲民法典》作為樣板法。除了統(tǒng)一法和樣板法形式之外,還有第三種模式,那就是先制定一部樣板法,然后經(jīng)過若干年的探索,再把它納入到國(guó)際公約之中。但是第二種模式和第三種模式的缺點(diǎn)是不能適用歐盟的法律制度,如果成員國(guó)頒布的成文立法,違反了《歐洲民法典》,歐盟委員會(huì)就不得根據(jù)《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69條的規(guī)定, 提起違法行為確認(rèn)之訴。當(dāng)然,和歐盟指令相比,統(tǒng)一法或樣板法更具有靈活性,它可以使起草者根據(jù)確定的日程去開展工作。筆者傾向于贊成《歐洲民法典》采取樣板法或者模范法的形式。
七、結(jié)論
近年來,歐洲統(tǒng)一大市場(chǎng)對(duì)成員國(guó)民法發(fā)展的影響日益強(qiáng)勁,歐盟已經(jīng)有許多指令迫使其成員國(guó)協(xié)調(diào)其國(guó)內(nèi)的合同法與侵權(quán)法。其他私法制度將是下一步協(xié)調(diào)的目標(biāo)。歐盟實(shí)現(xiàn)法律協(xié)調(diào)的手段很多,包括指令、條約和規(guī)章。許多歐洲學(xué)者認(rèn)為,目前所需要的就是制定一部《歐洲民法典》,以推動(dòng)歐洲民法的協(xié)調(diào);而且,目前時(shí)機(jī)已經(jīng)成熟。但是,反對(duì)意見認(rèn)為制定這樣一部民法典尚為時(shí)過早。
“人身關(guān)系Ⅱ”是一個(gè)出于好奇心的問題,與中國(guó)的立法和理論現(xiàn)狀無關(guān),它發(fā)生于閱讀外國(guó)文獻(xiàn)的譯文或原文的過程中。
在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xué)原理——權(quán)利的科學(xué)》第88頁中,有“對(duì)人權(quán)的原則”、“對(duì)人權(quán)(或人身權(quán))的性質(zhì)和取得”的標(biāo)題。所謂對(duì)人權(quán),指“占有另一人積極的自由意志,即通過我的意志,去規(guī)定另一個(gè)人的自由意志去做某種行為的力量”。(注:[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xué)原理——權(quán)利的科學(xué)》,沈叔平譯,商務(wù)印書館1991年版,第88頁。黑格爾為了反駁康德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觀點(diǎn),也使用了“康德所說人格權(quán),是根據(jù)契約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的表達(dá)。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范揚(yáng)、張企泰譯,商務(wù)印書館1961年版,第49頁。)不難看出,這樣的對(duì)人權(quán)實(shí)際上就是債權(quán),它肯定存在于一種叫做personalrelations的關(guān)系中,這種關(guān)系當(dāng)然也不是前節(jié)考察的personalrelations,因此我把它稱之為“人身關(guān)系Ⅱ”。
1871年阿根廷民法典的作者達(dá)爾馬修•薩爾斯菲爾德(DalmacioSarsfield)在其法典的第497條中規(guī)定:“所有的對(duì)人權(quán)(Derechopersonale)都與對(duì)人的義務(wù)相對(duì)應(yīng)。沒有與物權(quán)(Derechosreales)相對(duì)應(yīng)的債”。在這一條文中,薩爾斯菲爾德把對(duì)人權(quán)設(shè)定為與物權(quán)相對(duì)立的權(quán)利,顯然就是債權(quán)。在對(duì)該條的注釋中,他提到奧布瑞和勞(AubryyRau)在其著作的第296節(jié)中把這種區(qū)分追溯到法國(guó)民法典。稱:“法國(guó)民法典在將權(quán)利區(qū)分為對(duì)人權(quán)和對(duì)物權(quán)的同時(shí),也將義務(wù)區(qū)分為對(duì)人義務(wù)和對(duì)物義務(wù)”。(注:VéaseCodigoCivil,RepublicaArgentina,Zavalia,BuenosAires,1990,p.161.譯文參考了徐滌宇對(duì)該法典完成的未刊的中譯本,在此向徐滌宇致謝。)我未在法國(guó)民法典中找到作這種區(qū)分的明確條文,學(xué)者們很可能是在注釋該法典第1101條關(guān)于債的定義時(shí)根據(jù)當(dāng)時(shí)的學(xué)說演繹出了這樣的區(qū)分。
在同一注釋中,薩爾斯菲爾德還援引了奧托蘭(Ortolan)在其《概論》第67節(jié)中的話說明對(duì)人權(quán)和對(duì)物權(quán)各自的特征:“一個(gè)人單個(gè)地成為權(quán)利的消極主體時(shí),該權(quán)利為對(duì)人權(quán)。任何人均非單個(gè)地成為權(quán)利的消極主體時(shí),該權(quán)利為對(duì)物權(quán)。或更簡(jiǎn)單地說,一項(xiàng)權(quán)利賦予的權(quán)能乃是個(gè)別地約束某人供、給、提供某物或?qū)δ呈碌淖鳛椤⒉蛔鳛闀r(shí),為對(duì)人權(quán)。一項(xiàng)權(quán)利賦予的權(quán)能乃是或多或少地從某物中取得利益時(shí),為對(duì)物權(quán)”。(注:VéaseCodigoCivil,RepublicaArgentina,Zavalia,BuenosAires,1990,p.161.譯文參考了徐滌宇對(duì)該法典完成的未刊的中譯本,在此向徐滌宇致謝。)此語無非是說,相對(duì)于對(duì)物權(quán),對(duì)人權(quán)有一個(gè)特征:其義務(wù)主體是特定的而非不特定的,因此它是對(duì)人權(quán)而非對(duì)世權(quán)。這一特征與現(xiàn)代債的特征完全相合。
由于阿根廷具有使用“對(duì)人權(quán)”概念的傳統(tǒng),1998年12月18日完成并提交給司法部的《阿根廷共和國(guó)整合了商法典的民法典草案》仍保留了這一概念。這一草案的第4編為人身法(DelosDerechospersonales),實(shí)際上就是債法;第5編是物權(quán)法。(注:Cfr.ProyectodeCodigoCivildelaRepublicaArgentinaUnificadoconelCodigodeComercio,Abeledo-Perrot,BuenosAires,1999.)看來,時(shí)至今日,還有把“人身權(quán)”理解為債權(quán)的康德信徒存在。
由于債權(quán)被稱為“對(duì)人權(quán)”,債的關(guān)系當(dāng)然是Relacionespersonales(“人身關(guān)系”或“人的關(guān)系”),但這種關(guān)系還有別的名稱,按照意大利學(xué)者布爾兌茲(AlbertoBurdese)的說明,人法根據(jù)關(guān)涉的對(duì)象分為兩個(gè)方面,其一,家庭關(guān)系,這是非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包括夫妻關(guān)系、親子關(guān)系以及監(jiān)護(hù)和保佐關(guān)系;其二,狹義的民事關(guān)系(Relazioniciviliinsensostretto),它就是債的關(guān)系,具有財(cái)產(chǎn)內(nèi)容,換言之,它是對(duì)人的具有財(cái)產(chǎn)內(nèi)容的關(guān)系。(注:Cfr.A.Burdese,IlsistemadelcodicecivileArgentinoeladistinzionetradirittipersonaliereali(DalpensierodiTeixeiradeFreitasaQuellodiVelezSarsfield),InSandroSchipani(acuradi),DalmacioVelezSarsfieldeilDirittoLatinoamericano,CEDAM,Padova,1991,p.152.)
現(xiàn)在的問題是,這樣的“人身關(guān)系”是如何來的?
在我的閱讀范圍內(nèi),最早論述這一問題的作家是康德(1724年-1804年)。他把權(quán)利分為天賦的和獲得的兩類。獲得的權(quán)利分為3種,其一,物權(quán);其二,對(duì)人權(quán);其三,物權(quán)性的對(duì)人權(quán)。(注:康德,前引書,第74頁。)對(duì)人權(quán)依附的關(guān)系實(shí)際上就是債,嚴(yán)格說來,是合同之債,因?yàn)榭档略谡撌鲞@種債時(shí)只談到了合同。康德的影響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時(shí)代的其他法典如法國(guó)民法典和阿根廷民法典,乃至于現(xiàn)代的阿根廷民法典草案,都或暗或明地把債處理成對(duì)人關(guān)系。這種二分法安排可能反映了這樣的觀念:物權(quán)關(guān)系是單純的人與物的關(guān)系,債的關(guān)系是人與人的關(guān)系。
進(jìn)一步的問題是,康德的這種權(quán)利分類理論又是如何來的?答曰,從羅馬法來的!像為人身關(guān)系Ⅰ提供過理論來源一樣,作為一個(gè)無盡的寶庫,羅馬法也為人身關(guān)系Ⅱ提供了理論來源。人身關(guān)系Ⅰ來自羅馬法中的人法;人身關(guān)系Ⅱ則來自羅馬法中的訴訟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兩個(gè)來源的“人身關(guān)系”經(jīng)過若干年后會(huì)采取同樣的語詞形式,以至于需要很多的理論勞動(dòng)才能把兩者分開。
在羅馬法中,訴訟首先被分為對(duì)人之訴(Actioinpersonam)和對(duì)物之訴(Actioinrem)兩種,因契約或因非行產(chǎn)生的訴訟為對(duì)人訴訟,其中原告可要求相對(duì)人對(duì)他為給付,給付可能涉及到物(給),也可能不涉及到物(做);就物的歸屬提出爭(zhēng)議的訴訟是對(duì)物訴訟,其中原告可要求被告返還物或由原告估定的價(jià)金。可以看出,對(duì)人之訴不過是保護(hù)相對(duì)權(quán)的方式;對(duì)物之訴不過是保護(hù)絕對(duì)權(quán)的方式。羅馬法中尚無相對(duì)權(quán)與絕對(duì)權(quán)的范疇,但已包含其萌芽,相信后世學(xué)者就是根據(jù)對(duì)人之訴和對(duì)物之訴的劃分鑄造出相對(duì)絕對(duì)這對(duì)權(quán)利的范疇的。
這兩種訴訟的名稱包含著一個(gè)極為有趣的語言現(xiàn)象。Actioinpersonam的名稱意味著在蓋尤斯體系第1編人法中作為主體的persona在第3編訴訟中成了受他人訴權(quán)作用的客體,這無非表明了社會(huì)成員間互為主客體的共存關(guān)系(通俗的表達(dá)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由此發(fā)生了“消極主體”(Sujetopasivo)的表達(dá),與之對(duì)應(yīng)的是“積極主體”(Sujetopositivo)。事實(shí)上,只有積極主體才是主體,消極主體就是客體的意思。盡管如此,在persona作為客體的場(chǎng)合,它仍然保持了persona的名頭,沒有變成Res(物)。然而,不可思議的是,Actioinrem所保護(hù)的,除了名副其實(shí)的Res外,還包括身份權(quán)和家庭權(quán)!(注: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fēng)譯,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前者如它包括調(diào)查某人是生來自由人還是解放自由人的訴訟;后者如它包括關(guān)于認(rèn)領(lǐng)子女的訴訟,(注:優(yōu)士丁尼:《法學(xué)階梯》,徐國(guó)棟譯,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頁。)兩者分別關(guān)系到自由和家父兩個(gè)構(gòu)成人格的要素,它們完全應(yīng)在“人”的范疇之內(nèi),在這里卻進(jìn)入了“物”的范疇。之所以如此,乃因?yàn)閺牧x務(wù)人的數(shù)目和履行義務(wù)的方式看,這兩種身份權(quán)與物權(quán)并無區(qū)別。由此看來,在羅馬法中,persona、res與inpersona和inrem不同,前者表示主體、客體;后者已脫離其字面含義,表示相對(duì)、絕對(duì)而已。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chǔ)上,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康德及其追隨者要用對(duì)人權(quán)的術(shù)語來表征債權(quán)了:他們無非力圖以對(duì)人權(quán)的術(shù)語揭示債權(quán)的相對(duì)性。作為額外的收獲,我們還可以理解康德為何要把現(xiàn)代家庭法范圍內(nèi)的身份權(quán)(注:事實(shí)上,康德所說的這種權(quán)利與現(xiàn)代人說的家庭成員法意義上的身份權(quán)略有不同:這種權(quán)利還包括主人與家庭的仆人之間的關(guān)系。參見康德,前引書,第95頁,第102頁及以下。)叫作“物權(quán)性的對(duì)人權(quán)”(德文personlichenSachrechten,英文personalrightsinproperty)。按照康德的解說,它是像占有一個(gè)物一樣地占有一個(gè)人,但不把他當(dāng)作物來使用的權(quán)利。(注:康德,前引書,第74頁。)這種權(quán)利既不是產(chǎn)生于專橫的個(gè)人行為,也不是來自單純的契約,而是來自法律。它高于一切單純的物權(quán)和對(duì)人權(quán)。(注:康德,前引書,第94頁。)康德認(rèn)為對(duì)這種權(quán)利的界定是他在法學(xué)上的發(fā)現(xiàn),這一自我評(píng)價(jià)有一定道理。之所以說它只有“一定的”道理,乃因?yàn)檫@種權(quán)利在羅馬法中就以家父權(quán)的形式存在,在康德強(qiáng)調(diào)它是一種對(duì)人的占有的時(shí)候,尤其如此,因此,康德并非憑空打造出一種新權(quán)利。之所以說它“有道理”,首先因?yàn)榭档乱延幸庾R(shí)地把這種權(quán)利與家父權(quán)區(qū)別開來,因此強(qiáng)調(diào)前者的并非產(chǎn)生于個(gè)人的專橫行為的性質(zhì),由此揭示了現(xiàn)代身份權(quán)的平等性和作為平等性之表現(xiàn)的相互性。其次因?yàn)榭档陆o羅馬法中人法的第二個(gè)部分取了一個(gè)現(xiàn)代名稱,該名稱顯然是對(duì)對(duì)物之訴和對(duì)人之訴的名稱進(jìn)行反思后得出的。康德不滿意羅馬人把一個(gè)人法的主題放在對(duì)物訴訟中處理,于是加上“對(duì)人”的定語闡明其與人法的聯(lián)系;同時(shí),他又基于身份權(quán)與物權(quán)共有的絕對(duì)性給這種權(quán)利加上了“物權(quán)性”的定語。這種亦“物”亦“人”的權(quán)利前所未聞,當(dāng)然屬于“發(fā)現(xiàn)”,好壞不論。
為了把人身關(guān)系Ⅰ與人身關(guān)系Ⅱ區(qū)別開來,我們用中文中的一個(gè)“對(duì)”字表征了人從主體到客體的轉(zhuǎn)化。事實(shí)上,這個(gè)“對(duì)”只存在于拉丁文中(是對(duì)In的對(duì)譯),而在現(xiàn)代諸語言中,無論是人法部分的人身權(quán)還是物法部分的對(duì)人權(quán),恐怕寫出來都是Personenrechte,這當(dāng)然缺乏區(qū)別性而造成不便,因此,奧地利民法典寧愿把債權(quán)表述為“對(duì)人的物權(quán)”。這一法典的第2編物法(Sachenrechtes)下設(shè)兩個(gè)分編。其一,對(duì)物權(quán)(dinglichRechten),包括占有、所有權(quán)、抵押、役權(quán)和繼承;其二,對(duì)人的物權(quán)(德文personlichenSachrechten,英文personalrightsinproperty),實(shí)際上是關(guān)于債的規(guī)定,包括合同和侵權(quán)賠償。這一更有區(qū)別性的表達(dá)或許包含了黑格爾的勞動(dòng)。
黑格爾(1770年~1831年)在其《法哲學(xué)原理》(1821年出版)中,批判了康德的“Personenrechte就是債權(quán)”的觀點(diǎn),他認(rèn)為:“從客觀上說,根據(jù)契約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并不是對(duì)人的權(quán)利,而只是對(duì)在他的外部的某種東西或者他可以轉(zhuǎn)讓的某種東西的權(quán)利,即始終是對(duì)物的權(quán)利”。(注:黑格爾,前引書,第49頁。)這無非是說,債權(quán)的客體不是債務(wù)人而是債的標(biāo)的物,債務(wù)人不過是債權(quán)人與標(biāo)的物之間的中介。如果說物權(quán)關(guān)系是一個(gè)單賓語句,那么債權(quán)關(guān)系是一個(gè)雙賓語句,除了有債務(wù)人作為間接賓語,直接賓語是標(biāo)的物。相較于康德的觀點(diǎn),黑格爾的這種認(rèn)識(shí)無疑更具有分析性的眼光。如果我們忽視年代錯(cuò)誤的可能,我們看到奧地利民法典關(guān)于債的“對(duì)人的物權(quán)”的表達(dá)就是一個(gè)黑格爾式的雙賓語表達(dá)。因此,康德的破綻一旦被黑格爾瞧破,除了阿根廷人,就再也無人以康德的方式把債的關(guān)系表述為“人身關(guān)系”了。至少在德國(guó)法中,并不存在這種意義的“人身關(guān)系”。由此,人身關(guān)系才變成單一的、僅在主體法中存在的民法調(diào)整對(duì)象。
無論對(duì)康德還是對(duì)阿根廷人,我都難以理解他們?yōu)楹我艞壛_馬法中現(xiàn)成的債的概念而舍簡(jiǎn)就繁,采用一個(gè)無比費(fèi)解的“人身關(guān)系”的概念,我想他們是為了維持人法-物法兩分的理論結(jié)構(gòu)或立法結(jié)構(gòu),一旦采用債的概念,物法就將分解為若干部分,不能與人法形成整齊對(duì)仗的二元結(jié)構(gòu)。
四、“人身關(guān)系”Ⅲ考
前文中關(guān)于市民法和萬民法區(qū)分的說明已經(jīng)為本節(jié)埋下了伏筆。本文第2節(jié)第1小節(jié)已提到,羅馬人民為了滿足對(duì)外交往的需要,把自己的一些獨(dú)特制度界定為市民法,只能由羅馬市民適用;把其他具有普遍性的制度界定為萬民法,讓它們對(duì)外邦人開放。這樣的市民法包括14項(xiàng)制度,它們有:1.宗親關(guān)系;2.家父權(quán);3.夫權(quán)和對(duì)婦女的監(jiān)護(hù);4.20歲以上的人可以把自己出賣為奴;5.人格變更;6.被共有之奴隸由共有人之一解放時(shí)其他共有人的增加權(quán);7.對(duì)市民法的所有權(quán)和萬民法的所有權(quán)之承認(rèn);8.要式買賣;9.擬訴棄權(quán);10.取得時(shí)效;11.遺囑的形式;12.外國(guó)人不能接受遺產(chǎn)或遺贈(zèng);13.采用“我允諾”之形式的口頭債務(wù);14.不分遺產(chǎn)的共同體。舍此之外的其他羅馬私法都是萬民法,它們多是關(guān)于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
我們看到,被當(dāng)作具有“羅馬特色”的法理解的市民法的內(nèi)容部分是調(diào)整“人身關(guān)系”的(第1-5項(xiàng)市民法的制度直接如此,第6、7、12項(xiàng)間接如此),部分是關(guān)于法律行為的形式的(第8、9、11、13、14項(xiàng))。由此我們似乎可以說:一定意義上的市民法實(shí)際上是調(diào)整人身關(guān)系和法律行為形式的規(guī)范;一定意義上的萬民法實(shí)際上是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規(guī)范。羅馬人在法律沖突中奉行的原則是:涉及人身關(guān)系的事項(xiàng)適用當(dāng)事人的屬人法;涉及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事項(xiàng)適用屬地法,即羅馬法。
這樣的法律沖突處理產(chǎn)生在多個(gè)城邦并存的環(huán)境中,當(dāng)羅馬擴(kuò)張成一個(gè)橫跨歐亞非3洲的大帝國(guó)后,其存在空間已經(jīng)不多了。476年日耳曼人攻陷西羅馬帝國(guó)后,新來的日耳曼人與舊居民羅馬人各有各的法律,前者的文明程度遠(yuǎn)遠(yuǎn)不如后者,前者消受不了后者的文明的法律;后者承受不了前者野蠻的法律,于是,出于“同一法律制度的主體可以生活在根據(jù)不同的法律調(diào)整的私法關(guān)系中”(注:Cfr.Calasso,Medioevodeldiritto,I,Giuffrè,Milano,1954,p.110.)的信念,日耳曼人和羅馬人各自適用自己的法律,并不區(qū)分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而有不同的法律適用。這種狀況被稱為“種族法”時(shí)代,其中的“種族法”又被稱為“屬人法”(Personallaw)。(注:韓德培:《國(guó)際私法新論》,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必須注意,這個(gè)術(shù)語十分容易誤解,一不小心就會(huì)把它理解為專門調(diào)整人身關(guān)系的“人身法”。
在多民族頻繁交往的情況下依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不同而分別適用法律的局面直到14世紀(jì)才恢復(fù),其時(shí),巴托魯斯(Bartolus,1314年-1357年)提出了法則區(qū)別說。他把某個(gè)城市共和國(guó)的特別法稱為“法則”(Statuta),再把這些法則主要分為“人的法則”(Statutapersonalia)和“物的法則”(Statutarealia)。人的法則是屬人的,用來解決人的權(quán)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人的身份關(guān)系等問題;物的法則是屬地的,用來解決物權(quán)、法律行為的方式等問題。(注:韓德培,前引書,第54頁,另參見章尚錦:《國(guó)際私法》,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頁。)我們看到,在巴托魯斯的法則區(qū)別說中,人的法則就是調(diào)整主體資格和家庭關(guān)系的市民法分支;物的法則就是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市民法的分支。前者與“市民法”的范圍暗合;后者與“萬民法”的范圍暗合。巴托魯斯在創(chuàng)立其法則區(qū)別說時(shí),肯定考慮到了羅馬人以市民法和萬民法的劃分處理多民族交往關(guān)系的經(jīng)驗(yàn)并用來解決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饒有興味的是,按照其法則區(qū)別說,出于者的相互尊重,具有較小普遍性的“市民法”反而具有域外效力;具有較大普遍性的“萬民法”卻只有域內(nèi)效力。這是從法律沖突的角度作出的規(guī)定,相反,羅馬法中的市民法和萬民法更多地是從比較法角度作出的區(qū)分,讓人感不到羅馬的裁判官有接受外邦的人身關(guān)系規(guī)則的域外效力之問題,因此,外邦人的婚姻在羅馬始終是事實(shí)而不是法律。(注:優(yōu)士丁尼《法學(xué)階梯》1,10pr.規(guī)定的合法婚姻的第一個(gè)要件是當(dāng)事人都是羅馬市民。前引書,第39頁。)這樣的人身關(guān)系法的霸權(quán)性與法則區(qū)別說中的“人的法則”的相互性適成對(duì)照。
多民族的和平貿(mào)易交往造就了巴托魯斯的分裂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法則區(qū)別說,文明際的戰(zhàn)爭(zhēng)和征服這種特殊形式的交往則造就了伊斯蘭國(guó)家對(duì)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另一種區(qū)分。我們知道,伊斯蘭國(guó)家的民法典多為單純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法典,(注:1928-1936年制定的伊朗民法典是一個(gè)例外,它對(duì)人法和物法都作了規(guī)定,但顛倒了兩者的位置,是一部物頭人尾的民法典。第1編是財(cái)產(chǎn);第2編是人;第3編是證實(shí)請(qǐng)求權(quán)的證據(jù)。其作者是留學(xué)瑞士的阿里•阿克巴爾•達(dá)瓦爾(AliAkbarDavar),據(jù)說他很多地參照了法國(guó)民法典。這一結(jié)構(gòu)是對(duì)民法通則第2條關(guān)于民法調(diào)整對(duì)象之定義的忠實(shí)貫徹。SeeS.H.Amin,Introduction,IntheCivilecodeofIran,GeneralEditorDr.Eftikhar。)它們是在西方殖民者的壓力下追求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這些國(guó)家在這一財(cái)產(chǎn)法典之外往往另立調(diào)整人身關(guān)系的“Personalstatuslaw”(通常譯為“個(gè)人身份法”,實(shí)際上以譯成“人身法”為佳)或“Leggesullostatutopersonale”(關(guān)于人的法則的法律),以圖保留自己傳統(tǒng)的社會(huì)組織方式。立法者認(rèn)為,人身關(guān)系是“道”;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是“器”,器可隨西方變而道不可更易,因此,人身關(guān)系必須由固有法調(diào)整,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可以由繼受法調(diào)整。在這兩種法的對(duì)立中,我們又看到了羅馬法中的市民法與萬民法的對(duì)立的痕跡。尤其令我感到興味的是,在伊斯蘭國(guó)家的“人身法”的名稱中,有了地道的“身”的詞素(Status)。
“身”的詞素是否意味著身份關(guān)系?我們看一下使用了Personalstatus之表達(dá)的伊朗民法典即可知曉這一問題的答案。其序言第6條規(guī)定,關(guān)于人身(Personalstatus)的事項(xiàng),諸如結(jié)婚、離婚、能力和繼承的法律,伊朗臣民必須遵守,即使居住于國(guó)外也不例外。第7條規(guī)定,居住在伊朗領(lǐng)土內(nèi)的外國(guó)國(guó)民,在條約規(guī)定的范圍內(nèi),受他們臣屬的政府就其人身(Personalstatus)事項(xiàng)和能力頒布的法律以及就繼承權(quán)的類似事項(xiàng)頒布的法律的約束。毫無疑問,這兩個(gè)條文涉及的“能力”屬于“人格法”,結(jié)婚、離婚屬于“身份法”。因此可以說,在伊斯蘭法中,“身”的詞素的確與身份關(guān)系相對(duì)應(yīng),不過,這種身份關(guān)系的范圍與傳統(tǒng)的理解不同。至少在巴托魯斯的法則區(qū)別說中,繼承是屬于物法的(無遺囑的繼承依物之所在地法(注:韓德培主編,前引書,第54頁。)),在羅馬法中,(注:蓋尤斯:《法學(xué)階梯》,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頁。)在潘得克吞法中,(注:Cfr.BernardoWindscheid,Dirittodellepandette(Vol.I),trad.it.diCarloFaddaePaoloEmilioBensa,UTET,Torino,1925,p.41.)也是如此,(注:但在我國(guó),梁慧星教授把繼承法明確列為身份法,不知何所本?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而在前述奧地利民法典中,已把繼承處理成物法的內(nèi)容。
再看一部“人身法”的內(nèi)容,如何?索馬里的“關(guān)于人的法則的法律”分為4編,第1編是結(jié)婚和離婚;第2編是子女和扶養(yǎng);第3編是監(jiān)護(hù)、保佐和,其中除標(biāo)題所示內(nèi)容外,還規(guī)定了收養(yǎng)問題;第4編是遺產(chǎn)繼承。這些內(nèi)容與伊朗民法典的相應(yīng)內(nèi)容同多異少。異者,是增加了監(jiān)護(hù)、保佐以及由此而來的,外加收養(yǎng),這些也屬于傳統(tǒng)的“人身關(guān)系”的內(nèi)容。最值得強(qiáng)調(diào)的相同之處是索馬里把“繼承”也規(guī)定進(jìn)“人身法”。由此看來,伊斯蘭國(guó)家的“人身關(guān)系”具有自己的特色:繼承由于涉及太多的教義因素被增加到這類關(guān)系的名目下(注:關(guān)于伊斯蘭繼承法中的教義因素,參見吳云貴:《伊斯蘭教法概略》,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這部分法是阿拉伯部落慣例與《古蘭經(jīng)》律例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于是,人身關(guān)系Ⅲ除了有“人”、“身”的因素外,還有了“物”(遺產(chǎn))的因素。正因?yàn)橛羞@樣的添加,人身關(guān)系Ⅲ才把自己與人身關(guān)系Ⅰ,Ⅱ區(qū)別開來。但我們也可看到,這樣的“人”、“身”、“物”具有把它們統(tǒng)一起來的共同的精神:伊斯蘭的精神。因此,如果說人身關(guān)系Ⅰ,Ⅱ僅僅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而人身關(guān)系Ⅲ則是交織著人與神的關(guān)系的人與人的關(guān)系。
五、結(jié)論
在考察3種人身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現(xiàn)在可以得出一些結(jié)論了。
首先回答序言中提出的問題:民法確實(shí)既調(diào)整人格關(guān)系,又調(diào)整身份關(guān)系。在早期,身份關(guān)系作為人格關(guān)系的要素存在,從奧地利民法典開始直到伊斯蘭國(guó)家的“人身法”,身份關(guān)系開始取得了與人格關(guān)系相并列的存在。
在我考察的諸立法例與學(xué)說的范圍內(nèi),人身關(guān)系Ⅰ是主體法和家庭法的規(guī)制對(duì)象,人身關(guān)系Ⅱ是債法的規(guī)制對(duì)象,人身關(guān)系Ⅲ是家庭法和繼承法規(guī)制的對(duì)象,它雖然來自人身關(guān)系Ⅰ但又不同于其母本。
人身關(guān)系是什么?首先,在基本的意義上,它表示不通過物的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與通過物的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形成對(duì)立。其次,人身關(guān)系涉及民族的文化宗教傳統(tǒng)較多,表示一個(gè)民族的生活中較多個(gè)性的部分,正猶如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表示一個(gè)民族生活中較多普遍性的部分,因此,一個(gè)國(guó)家的市民法,其財(cái)產(chǎn)法直接從外國(guó)引進(jìn)或請(qǐng)外國(guó)人起草都是可以容忍的,但對(duì)人身法卻不能這樣做。因此,在交往的環(huán)境中,人身關(guān)系法往往是固有法,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法,尤其是其中的債法,往往是繼受法。最后,與上一點(diǎn)相聯(lián)系,人身關(guān)系往往是一個(gè)民族需要屬人適用的那部分生活關(guān)系;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則可以聽任屬地法之適用。
人身關(guān)系可以分解為“人格關(guān)系”和“身份關(guān)系”兩個(gè)部分。在我考察的選言支的范圍內(nèi),人格關(guān)系中的“人格”從來不是,到現(xiàn)在也不應(yīng)是“人格權(quán)”的意思,而是某個(gè)市民社會(huì)的主體的意思或法律能力的擁有者的意思。“人格”應(yīng)該是“人格權(quán)”的基礎(chǔ),基礎(chǔ)與建立在基礎(chǔ)上的事物不可混同。所幸的是,近年來我國(guó)有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看到了“人格”與“人格權(quán)”的這種關(guān)系,拋棄了多年來關(guān)于“人格”的謬見。
在身份關(guān)系問題上我們犯的錯(cuò)誤更多,我們已把它縮減為“親屬關(guān)系”。從本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現(xiàn)代民法中,親屬關(guān)系不失為一類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在它的旁邊存在著的另類的身份,其一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外國(guó)人等影響法律能力的身份;其二是與前類身份相交錯(cuò)的弱者的身份,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同時(shí)也是這一類型的身份,在消費(fèi)者運(yùn)動(dòng)的沖擊下,這類中還出現(xiàn)了“消費(fèi)者”這樣的身份,所有這些身份都是代表弱勢(shì)群體的符號(hào),法律也基于這一現(xiàn)實(shí)給這類身份的擁有者以特殊的保護(hù)。從“契約到身份”的運(yùn)動(dòng),就是這種身份的崛起,民法就是在調(diào)整這種身份(例如意大利民法典根據(jù)歐共體指令作出的關(guān)于“消費(fèi)合同”的規(guī)定)的過程中得到其在20世紀(jì)的發(fā)展的。遺憾的是,這樣的立法和司法現(xiàn)實(shí)并未在理論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身份仍只被理解為“親屬關(guān)系”。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把兩類身份關(guān)系統(tǒng)一到民法調(diào)整的身份關(guān)系上來的時(shí)候了。從此我們可以宣稱,民法不僅調(diào)整親屬法上的身份關(guān)系,而且還調(diào)整親屬法外的身份關(guān)系。后一種身份除了其涉及到保護(hù)弱者的部分外,就是權(quán)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問題。
由人格關(guān)系和身份關(guān)系合成的人身關(guān)系的功能如何?我的回答是:組織一個(gè)不能離開財(cái)產(chǎn)的市民社會(huì)。這一表達(dá)的中心詞是市民社會(huì),其限定語表明了它不能離開財(cái)產(chǎn)而存在。那么,什么是人身關(guān)系法組織的市民社會(huì)?從字面來看,市民社會(huì)首先是一個(gè)人的社會(huì)(即使所有的人都是商品生產(chǎn)者,它也是一個(gè)商品生產(chǎn)者的社會(huì),而不是商品本身的社會(huì)),其組織包括兩個(gè)環(huán)節(jié)。第一個(gè)環(huán)節(jié)是對(duì)人進(jìn)行分類:首先,身份法通過國(guó)民與外國(guó)人的身份劃分把“我們”(本市民社會(huì))與“他們”(其他市民社會(huì))分開,賦予全部的“我們”和一定的“他們”以行為能力,這是人法的對(duì)外方面,因?yàn)槿祟惒皇且粋€(gè)共同體,而是共同體的總和,中國(guó)只是其中的一個(gè),內(nèi)外應(yīng)有所別;其次,它運(yùn)用身份劃分在某個(gè)共同體內(nèi)把人分為不同的類別作為法律適用的基準(zhǔn)。第二個(gè)環(huán)節(jié)是分別給予不同身份的人不同的待遇;或賦予完全的行為能力,或限制其這方面的能力,所以我們說行為能力制度也是身份法的一個(gè)內(nèi)容,其本質(zhì)在于它是組織一個(gè)社會(huì)的工具。通過以上作出的身份分類,立法者力圖做到“老有所養(yǎng)、幼有所育、壯有所用”。市民的生老病死皆有所靠,依靠的就是和自己一樣的市民,按照我的理解,市民社會(huì)就是一個(gè)盡量自足、有問題盡量靠自己解決、尤其不求助于國(guó)家的社會(huì),行為能力制度、監(jiān)護(hù)和保佐制度、扶養(yǎng)制度等等,都是市民社會(huì)完成自己的組織功能的工具。理解了這一點(diǎn),就可以理解如下的民法調(diào)整對(duì)象定義:
“所有可以在民法的名號(hào)下包括的東西,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更直接地關(guān)系到主體的存在的規(guī)則;其次是上述主體參與享用和利用經(jīng)濟(jì)資源的一般規(guī)則”(注:Cfr.L.BigliazziGerietal.,DirittoCivile,1,Normesoggettierapportogiuridico,UTET,Torino,1987,p.13.AnchesivediNuovoDizionarioGiuridico,acuradiFedericodelGiudice,EdizioneSimone,Napoli,1998,lavocedidirittocivile.)。
民法是“調(diào)整主體際關(guān)系的法,這些主體可以是個(gè)人,也可以是私人團(tuán)體,甚至在實(shí)現(xiàn)單個(gè)的規(guī)范時(shí),這些關(guān)系也并不托付給公共機(jī)構(gòu)的照料,而是留諸個(gè)人的主動(dòng)性。因此,這一法的部門包括所有關(guān)系到主體的存在、其能力的規(guī)范,以及上述主體參與對(duì)經(jīng)濟(jì)資源的享有和利用的各個(gè)方面的規(guī)則。它尤其包括對(duì)物權(quán)和債的關(guān)系的規(guī)制。最后,它還包括在其遭受法律——財(cái)產(chǎn)領(lǐng)域的偶然或現(xiàn)實(shí)的侵害時(shí)保護(hù)主體的規(guī)范。”(注:FedericodelGiudice,NuovoDizionarioGiuridico,EdizioneSimone,Napoli,1998,p.430.)
民法“不考慮其業(yè)務(wù)和職業(yè)地調(diào)整在其自身關(guān)系和與國(guó)家的關(guān)系中的人,而這些關(guān)系以滿足人性的需要為目的”。(注:VéaseJorgeJoaquinLlambias,TratadodeDrechoCivil,partegeneral,tomoI,EditorialPerrot,BuenosAires,1997,p.40.)
這些拉丁語族國(guó)家的民法調(diào)整對(duì)象定義都強(qiáng)調(diào)民法的首要功能是組織法,其次才是解決經(jīng)濟(jì)資源的享有和利用問題的法。這與德國(guó)法族把民法理解為單純的財(cái)產(chǎn)法的傾向適成對(duì)照,與在我國(guó)長(zhǎng)期流行的民法通則第2條式的民法調(diào)整對(duì)象理解適成對(duì)照。
內(nèi)容提要: 私法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不僅運(yùn)用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和債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還依賴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遵循“依身定份”準(zhǔn)則,利用身份崗位與身份體系結(jié)構(gòu)對(duì)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做出安排,通過身份秩序規(guī)范財(cái)產(chǎn)秩序。身份調(diào)整的機(jī)理是,身份關(guān)系主導(dǎo)并塑造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適應(yīng)并滿足身份關(guān)系的要求。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在非市場(chǎng)化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和市場(chǎng)主體內(nèi)部組織化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領(lǐng)域具有比較優(yōu)勢(shì),在財(cái)產(chǎn)的形成、取得、支配與變動(dòng)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功能。社會(huì)共同體中依據(jù)身份政策配置財(cái)產(chǎn),生產(chǎn)共同體中運(yùn)用身份權(quán)力規(guī)范財(cái)產(chǎn)秩序,生活共同體中依據(jù)身份關(guān)系安排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個(gè)人身份在市場(chǎng)中形成無形財(cái)產(chǎn)。
一、引言:傳統(tǒng)民法財(cái)產(chǎn)理論的結(jié)構(gòu)缺失和身份調(diào)整
傳統(tǒng)民法理論認(rèn)為,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主要依賴物權(quán)法與債權(quán)法。物權(quán)法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的歸屬與利用關(guān)系,維護(hù)財(cái)產(chǎn)的靜態(tài)秩序;債權(quán)(主要是契約,下文與契約通用)法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的流轉(zhuǎn)關(guān)系,維護(hù)財(cái)產(chǎn)的動(dòng)態(tài)秩序。這種理論依據(jù)市場(chǎng)交易的需要而設(shè)計(jì),對(duì)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遵循交易導(dǎo)向,其基本原則是等價(jià)有償,在市場(chǎng)交易領(lǐng)域內(nèi)具備邏輯的自洽性和功能的完備性。[1]然而,私法中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并非僅僅包含市場(chǎng)化的部分,也包含非市場(chǎng)化的部分;在市場(chǎng)化領(lǐng)域,不僅包含交易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還包括市場(chǎng)主體內(nèi)部的組織化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在這些領(lǐng)域中,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存在狀態(tài)、利益配置方式、價(jià)值取向、運(yùn)行機(jī)制、制度規(guī)則均不能完全契合于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和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與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不足以有效規(guī)范財(cái)產(chǎn)秩序,從而出現(xiàn)了法律調(diào)整的空白地帶。對(duì)此,現(xiàn)有財(cái)產(chǎn)法理論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
財(cái)產(chǎn)法理論的結(jié)構(gòu)缺失進(jìn)一步誘發(fā)了民法理論與制度的系列缺陷,體現(xiàn)在無法妥善協(xié)調(diào)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與人身關(guān)系之間的矛盾,導(dǎo)致民法總論與總則的功能局限。由于在片面的財(cái)產(chǎn)規(guī)則的基礎(chǔ)上設(shè)計(jì)民法總則,因此以《德國(guó)民法典》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guó)家民法典總則編中關(guān)于人、物、法律行為、、期間、權(quán)利行使等規(guī)定,均不能適用于人身法。[2]傳統(tǒng)理論無視財(cái)產(chǎn)行為與人身行為的不同,單純?cè)谪?cái)產(chǎn)行為基礎(chǔ)上設(shè)計(jì)法律行為,并試圖用于全部的私法關(guān)系。結(jié)果,《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通則》有關(guān)法律行為的許多規(guī)定大部分都只能適用于財(cái)產(chǎn)行為而不能適用于人身行為。[3]可見,財(cái)產(chǎn)法理論缺陷與機(jī)制缺失導(dǎo)致傳統(tǒng)民法理論體系以及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法體系存在著邏輯斷裂:民法總則不能有效統(tǒng)領(lǐng)分則的全部?jī)?nèi)容;人身關(guān)系與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之間的聯(lián)系被割裂,人身關(guān)系與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之間缺乏溝通機(jī)制。
這種理論和制度上的缺陷如何彌補(bǔ)?我們只能在物權(quán)、契約之外去尋找能夠溝通人身關(guān)系與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并填補(bǔ)財(cái)產(chǎn)法空白領(lǐng)域的法律調(diào)整機(jī)制,這個(gè)機(jī)制就是身份。[4]由于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復(fù)雜多樣性,客觀上要求私法提供多種調(diào)整機(jī)制,每種調(diào)整機(jī)制在其固有功能領(lǐng)域具備比較優(yōu)勢(shì),相互不可替代。對(duì)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發(fā)揮調(diào)整功能的私法調(diào)整機(jī)制主要包括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和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在某一種特定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中,只有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才能進(jìn)行有效調(diào)整;并且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既調(diào)整人身關(guān)系又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通過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在人身行為與財(cái)產(chǎn)行為之間形成聯(lián)系、滲透與互補(bǔ)關(guān)系。
然而,在現(xiàn)有民法理論研究中,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長(zhǎng)期被忽視。學(xué)者們沒有認(rèn)真研究私法中的身份如何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的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狀態(tài)。由于私法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內(nèi)部的調(diào)整機(jī)制沒有理清,我們也無法解釋民法與商法、經(jīng)濟(jì)法在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和調(diào)整機(jī)制方面的區(qū)分、聯(lián)系與協(xié)調(diào)。在既有的私法制度規(guī)則中,雖然客觀上存在著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身份對(duì)財(cái)產(chǎn)的形成、取得、支配、分配均發(fā)揮不可替代的調(diào)整功能,但立法者并未有意識(shí)地進(jìn)行身份制度規(guī)則設(shè)計(jì),在私法構(gòu)造中仍忽視、擠壓并掩蓋身份。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對(duì)私法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在理論上加以闡釋說明。
二、私法上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身份調(diào)整的基本原理
1.私法上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的界定
私法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是指在私法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領(lǐng)域中身份作為一種基本的調(diào)整機(jī)制發(fā)揮作用,遵循“依身定份”準(zhǔn)則,借助身份與身份體系結(jié)構(gòu)對(duì)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做出安排,通過身份秩序規(guī)范財(cái)產(chǎn)的形成、取得、支配與變動(dòng)秩序。
某些私法領(lǐng)域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其本質(zhì)并非交易性的,只能通過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調(diào)整,因而屬于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的固有調(diào)整領(lǐng)域。在財(cái)產(chǎn)生成關(guān)系中,通過市場(chǎng)評(píng)價(jià),個(gè)人身份本身成為一種無形財(cái)產(chǎn),不同的身份形成不同份額的無形財(cái)產(chǎn)。在財(cái)產(chǎn)歸屬關(guān)系中,所有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是主導(dǎo)機(jī)制,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是輔助機(jī)制。在財(cái)產(chǎn)利用關(guān)系中,他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是基礎(chǔ)機(jī)制,為財(cái)產(chǎn)的利用提供前提性法律條件,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則直接協(xié)調(diào)財(cái)產(chǎn)的社會(huì)化運(yùn)作,是現(xiàn)代社會(huì)中財(cái)產(chǎn)運(yùn)用的實(shí)現(xiàn)機(jī)制。[5]而處于身份體[6]中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基本調(diào)整機(jī)制為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的基本調(diào)整機(jī)制。私法依據(jù)身份體的特定功能要求設(shè)計(jì)不同的身份體系,通過身份職權(quán)、職責(zé)的履行形成身份體內(nèi)部的財(cái)產(chǎn)秩序,滿足其成員的利益要求。在家庭生活中,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配置家庭所擁有的生活資源,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需要,農(nóng)村家庭身份秩序還安排生產(chǎn)秩序。在職業(yè)社團(tuán)中,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將人的要素與生產(chǎn)資料進(jìn)行整合,形成生產(chǎn)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能力;不同身份意味著對(duì)財(cái)產(chǎn)與人力資源組合享有不同范圍的支配權(quán),也意味著對(duì)生產(chǎn)產(chǎn)出擁有份額不同的分享權(quán)。總之,在社會(huì)分配中,法律通過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彌補(bǔ)市場(chǎng)缺陷,依據(jù)財(cái)產(chǎn)標(biāo)準(zhǔn)對(duì)市場(chǎng)所產(chǎn)生的身份差異進(jìn)行矯正。
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具有特殊的功能。只有在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中,我們才能發(fā)現(xiàn)身份的無形財(cái)產(chǎn)化,理解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新的財(cái)富形成機(jī)制與存在形式:在生產(chǎn)領(lǐng)域,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協(xié)調(diào)了財(cái)產(chǎn)的社會(huì)化運(yùn)作;在生活關(guān)系中,實(shí)現(xiàn)了財(cái)產(chǎn)對(duì)人身關(guān)系和人的生活需要的滿足;在再分配領(lǐng)域,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彌補(bǔ)了市場(chǎng)機(jī)制的不足,衡平了人們之間的利益關(guān)系,為強(qiáng)者配置財(cái)產(chǎn)義務(wù),為弱者提供符合文明性生存的最低生活保障。由于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的存在,私法機(jī)制更切合現(xiàn)實(shí)生活,并且通過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溝通了市場(chǎng)關(guān)系與生活關(guān)系的各個(gè)方面,實(shí)現(xiàn)了民法與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商法、經(jīng)濟(jì)法的無縫連接。
2.私法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身份調(diào)整的機(jī)理
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擁有不同于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和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的特殊調(diào)整機(jī)理,其內(nèi)容是:身份關(guān)系主導(dǎo)并塑造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適應(yīng)并滿足身份關(guān)系的需要。
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本質(zhì)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人與人之間存在各種身份聯(lián)系,財(cái)產(chǎn)也被不同的身份體系所安排,存在于穩(wěn)定的身份結(jié)構(gòu)框架中,嵌入相應(yīng)的身份關(guān)系之中。每一個(gè)具體身份結(jié)構(gòu)中的人對(duì)財(cái)產(chǎn)擁有特定的歸屬、支配權(quán)益,遵循特定的行為規(guī)則,通過個(gè)人意志與社會(huì)意志對(duì)特定財(cái)產(chǎn)按照需要進(jìn)行支配。這為各種身份結(jié)構(gòu)框架中的財(cái)產(chǎn)安排奠定了鞏固的制度基礎(chǔ),通過不同的制度結(jié)構(gòu)提供不同的功能保障,滿足人民生活的特定需要,確保市民生活安全。這種制度結(jié)構(gòu)在社會(huì)生活中反復(fù)應(yīng)用,在立法中獲得強(qiáng)行法的保障,是人們進(jìn)行財(cái)產(chǎn)活動(dòng)的默示條件。
市民生活關(guān)系中的財(cái)產(chǎn)具有兩個(gè)層面的屬性:一個(gè)層面是將財(cái)產(chǎn)看做抽象的、同質(zhì)的財(cái)產(chǎn)。財(cái)產(chǎn)的擁有者和支配者被看做抽象的個(gè)人,也不考慮權(quán)利人對(duì)特定財(cái)產(chǎn)的具體生活需要。這個(gè)層面的財(cái)產(chǎn)具有交易屬性,各種形態(tài)的財(cái)產(chǎn)均具有價(jià)值,可以通過貨幣進(jìn)行量化。“不論以商人為媒介進(jìn)行商品交換的各生產(chǎn)部門的社會(huì)組織如何,商人的財(cái)產(chǎn)總是作為貨幣財(cái)產(chǎn)而存在,他的貨幣也總是作為資本執(zhí)行職能。”[7]財(cái)產(chǎn)的抽象、同質(zhì)屬性在諸多法律制度規(guī)則中發(fā)揮出功能上的優(yōu)勢(shì)。通過對(duì)財(cái)產(chǎn)進(jìn)行抽象化、同質(zhì)化處理的法律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市場(chǎng)交易,私法的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和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就是建立在這種技術(shù)之上。另一個(gè)層面是財(cái)產(chǎn)總是具體情景、結(jié)構(gòu)中的財(cái)產(chǎn),每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均存在特定的用途,即使在交易領(lǐng)域也是如此。身份關(guān)系中的財(cái)產(chǎn)不再是抽象的,而是為特定的人、特定的生產(chǎn)生活需要而存在的;財(cái)產(chǎn)不再是同質(zhì)的,而是嵌入特定的身份體之中,按照特定用途塑造,每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均具備特定的功能,彼此存在個(gè)性差異。財(cái)產(chǎn)的異質(zhì)化對(duì)應(yīng)著沒有進(jìn)入交易或者完成交易之后階段的財(cái)產(chǎn)存在狀態(tài)。私法在此基礎(chǔ)上運(yùn)用身份技術(shù)設(shè)計(jì)法律規(guī)則,根據(jù)這種差異性要求進(jìn)行差別調(diào)整,形成了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
3.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身份調(diào)整的一般原則
身份調(diào)整遵循特有的法律原則,這些原則不同于物權(quán)和契約調(diào)整的原則。
(1)功能導(dǎo)向原則,即財(cái)產(chǎn)對(duì)身份關(guān)系的合目的性。換言之,特定的身份關(guān)系塑造了相應(yīng)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法律屬性,任何身份體中存在的單項(xiàng)財(cái)產(chǎn)或財(cái)產(chǎn)組合均具有特定的用途;財(cái)產(chǎn)是為了維持身份體的存在、運(yùn)作及滿足個(gè)體在身份關(guān)系中的特定需要而存在。例如,家庭財(cái)產(chǎn)就是為了滿足家庭成員基本生活需要,企業(yè)財(cái)產(chǎn)是為了滿足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需要,社區(qū)的財(cái)產(chǎn)是為了滿足社區(qū)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社會(huì)福利財(cái)產(chǎn)是為了保障公民基本福利和弱勢(shì)群體基本生存需要。
身份財(cái)產(chǎn)負(fù)載特定的功能,每種財(cái)產(chǎn)上所承載的特定功能塑造了相應(yīng)的財(cái)產(chǎn)結(jié)構(gòu)、價(jià)值取向、運(yùn)作機(jī)理,遵循相應(yīng)的制度規(guī)則。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與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中的財(cái)產(chǎn)針對(duì)交易,財(cái)產(chǎn)通過貨幣同質(zhì)化,在一般交易領(lǐng)域?qū)崿F(xiàn)了財(cái)產(chǎn)的去身份化和去功能化,提供了市場(chǎng)交易的基礎(chǔ)性法律條件。但是,僅憑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與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的設(shè)計(jì)無法適應(yīng)復(fù)雜的市場(chǎng)關(guān)系,對(duì)財(cái)產(chǎn)的社會(huì)化交易(信用證)和社會(huì)化組織(公司)所提出的法律訴求無法回應(yīng)。商法運(yùn)用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按照具體的財(cái)產(chǎn)性質(zhì)和功能要求進(jìn)行安排,提供了市場(chǎng)交易的技術(shù)性法律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bǔ)民法理論與規(guī)則的不足。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傳統(tǒng)民法制度規(guī)則設(shè)計(jì)忽視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但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卻能夠持續(xù)發(fā)展。
(2)權(quán)力主導(dǎo)原則。傳統(tǒng)理論認(rèn)為私法是權(quán)利法,并且這種權(quán)利主體是獨(dú)立平等的抽象人。在市場(chǎng)中,主體人格獨(dú)立,行為自主,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歸屬明確,有利于調(diào)動(dòng)人們的積極性與創(chuàng)造性;平等協(xié)商是形成相互關(guān)系的主要手段。但是,市民生活關(guān)系甚至是市場(chǎng)關(guān)系并非僅僅是交易關(guān)系,在其他社會(huì)關(guān)系領(lǐng)域,在平等協(xié)商模式之外,還存在“管理與被管理”、“命令與服從”關(guān)系,這是權(quán)力機(jī)制的存在基礎(chǔ)。在身份調(diào)整的領(lǐng)域,其財(cái)產(chǎn)秩序的形成和維護(hù)主要借助身份權(quán)力秩序,在身份體內(nèi)部回應(yīng)差異化的調(diào)整要求,私法采用權(quán)力技術(shù),賦予優(yōu)勢(shì)身份者更大的權(quán)力,支配特定范圍的人力與財(cái)產(chǎn)資源,協(xié)調(diào)身份體內(nèi)部運(yùn)作關(guān)系,通過身份權(quán)力保障身份體的整體效率。從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角度分析,這種權(quán)力模式可以節(jié)約協(xié)商成本,相對(duì)于平等協(xié)商模式具有效率上的比較優(yōu)勢(shì)。
(3)倫理優(yōu)先原則。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與人倫關(guān)系[8]是兩個(gè)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領(lǐng)域,財(cái)產(chǎn)行為與人身行為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純粹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領(lǐng)域奉行效率優(yōu)先,遵循等價(jià)有償原則;身份關(guān)系領(lǐng)域奉行倫理優(yōu)先原則。在由身份調(diào)整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領(lǐng)域,基本做法是通過身份秩序規(guī)范財(cái)產(chǎn)秩序,因此身份在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時(shí)奉行倫理優(yōu)先原則。財(cái)產(chǎn)處于不同身份關(guān)系之中,滿足人們不同層次的生活需要,如生存需要、營(yíng)利需要;不同層次的生活利益依據(jù)倫理規(guī)則在法律上獲得不同的保護(hù)力度。一般認(rèn)為,人的生存利益優(yōu)先于商業(yè)利益;基本生存利益優(yōu)先于其他生活利益;在企業(yè)財(cái)產(chǎn)分配關(guān)系中,勞動(dòng)所得優(yōu)先于資本所得;間接融資的債權(quán)優(yōu)于直接融資的股權(quán)。[9]在對(duì)這些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處理的過程中,一般通過確立優(yōu)先順序保障某些身份利益的優(yōu)越地位,如破產(chǎn)分配中的職工工資福利債權(quán)具有優(yōu)先效力。
(4)人格謙抑原則。身份關(guān)系中的人處于各種聯(lián)系和差序格局中,注重相互之間的差異與互補(bǔ)關(guān)系,身份調(diào)整的技術(shù)性特質(zhì)要求對(duì)人與財(cái)產(chǎn)進(jìn)行綜合支配、統(tǒng)一安排,突破了“人格-財(cái)產(chǎn)”的絕對(duì)界限。如果絕對(duì)地強(qiáng)調(diào)人格的獨(dú)立、自由、尊嚴(yán),那么,許多身份關(guān)系無法維持,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無法調(diào)整。因此,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的目的并非為了突出個(gè)人人格,也不在于規(guī)定一個(gè)“人之為人”的統(tǒng)一底線,人格制度只是作為一種前提性的制度發(fā)揮作用,個(gè)人人格本身需要謙抑。近代以來所奉行的社會(huì)理念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10]這種理念表彰了基本倫理價(jià)值,注重人格的獨(dú)立、自由、尊嚴(yán),保證個(gè)體在社會(huì)生活中的廣泛平等。“所以法的命令是:‘成為一個(gè)人,并尊重他人為人。’”[11]并且人本身不能成為支配對(duì)象,德國(guó)民法學(xué)家拉倫茨就認(rèn)為,支配權(quán)的客體既不能是自己,也不能是他人。[12]人身權(quán)從實(shí)質(zhì)上看是一種受尊重的權(quán)利,一種人身不可侵犯的權(quán)利,人身權(quán)不是支配權(quán)。[13]“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理念僅具有有限的合理性,[14]并不完全符合事實(shí),在私法制度中也一直無法排除對(duì)人的支配。例如,羅馬法上家長(zhǎng)權(quán)的支配力概括地及于屬于該家族的人和物。對(duì)人的支配是身份法中的基本技術(shù)。在復(fù)雜的市民生活關(guān)系中,有些領(lǐng)域不存在完全獨(dú)立、自由的人格與絕對(duì)的意思自治。在社會(huì)治理和秩序形成中,必然會(huì)導(dǎo)致一些人管理支配另一些人,即存在“命令-服從關(guān)系”。在這些領(lǐng)域,由于個(gè)體能力缺乏或者個(gè)體之間存在比較效率優(yōu)勢(shì)等原因,個(gè)體之間直接的平等協(xié)商難以適用。古代家庭中的家長(zhǎng)權(quán)、現(xiàn)代企業(yè)中的經(jīng)理權(quán)就屬于這種情形。對(duì)人支配權(quán)指向他人的行為或者人身利益,這種對(duì)人的權(quán)利主要存在于身份權(quán)之中,如配偶權(quán)中權(quán)利人對(duì)對(duì)方性利益的約束,親權(quán)中對(duì)未成年子女的管教等方面就包含著對(duì)人的支配內(nèi)容。史尚寬先生也認(rèn)為:“支配權(quán)包括物權(quán)、無體財(cái)產(chǎn)權(quán)及親屬權(quán)。”[15]其實(shí),在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中所體現(xiàn)的對(duì)人支配,有些目的在于彌補(bǔ)被支配者的能力不足,有些目的在于進(jìn)行社會(huì)化協(xié)作以獲得更高的效率,只是對(duì)被支配者的自由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進(jìn)行限制,并非必然導(dǎo)致對(duì)人格獨(dú)立、自由、尊嚴(yán)的否定。
4.私法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三種調(diào)整機(jī)制之間的關(guān)系
私法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三種調(diào)整機(jī)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得到法學(xué)界不同程度的關(guān)注,從而處于不同地位;他們各自遵循自身的內(nèi)在邏輯,擁有各自的優(yōu)勢(shì)領(lǐng)域,相互補(bǔ)充以有效規(guī)范私法財(cái)產(chǎn)秩序。
在民法理論中,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與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屬于顯性機(jī)制,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屬于隱性機(jī)制。在古代社會(huì)中,法律直接規(guī)定了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依身定份”的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是財(cái)產(chǎn)領(lǐng)域的顯性機(jī)制。在近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興起的過程中,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變成隱性機(jī)制。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財(cái)產(chǎn)的主要形態(tài)是有體物,土地是主要財(cái)產(chǎn)形式,財(cái)產(chǎn)法律制度設(shè)計(jì)對(duì)象是市場(chǎng)交易中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私法學(xué)者用物權(quán)和債權(quán)二元機(jī)制解釋財(cái)產(chǎn)法制度規(guī)則。但是,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與債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從來不曾取代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在私法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需要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的領(lǐng)域,立法者會(huì)不自覺地設(shè)計(jì)出身份制度規(guī)則。企業(yè)中的大量制度規(guī)范就屬于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因此,財(cái)產(chǎn)法中的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一直存在、發(fā)展并發(fā)揮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學(xué)者關(guān)注,更未得到理論解釋,自然屬于隱性機(jī)制。
三種調(diào)整機(jī)制之間功能互補(bǔ)。在近代以來,立法者利用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與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的二元性財(cái)產(chǎn)調(diào)整模式基本能夠調(diào)整市場(chǎng)中大部分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其間,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在默默地發(fā)揮作用。這種格局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顯示了局限性。因?yàn)樨?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種類和結(jié)構(gòu)復(fù)雜化,人身權(quán)利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之間的轉(zhuǎn)化渠道增加,兩者之間的權(quán)利界限模糊,單純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與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不足以規(guī)范這些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需要強(qiáng)化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才能夠有效保障財(cái)產(chǎn)秩序。在現(xiàn)代民法理論中,應(yīng)該界定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與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的功能邊界,進(jìn)一步重視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的研究,可以恢復(fù)社會(huì)生活的真實(shí)場(chǎng)景,消除財(cái)產(chǎn)法理論與事實(shí)關(guān)系之間的矛盾。例如,社會(huì)中存在的大量未成年人,一般都不享有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也不締結(jié)交易契約,其生活依賴于其父母履行撫養(yǎng)義務(wù),即依據(jù)身份聯(lián)系所提供的利益而生活。單純通過物權(quán)調(diào)整機(jī)制與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既無法解釋未成年人的生存關(guān)系,也無法保障其生存利益。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的研究還有利于準(zhǔn)確理解財(cái)產(chǎn)法立法中一些問題的性質(zhì),合理配置其制度功能。例如,夫妻財(cái)產(chǎn)制度的特質(zhì)在于夫妻財(cái)產(chǎn)服從夫妻關(guān)系。夫妻之間的相互扶助義務(wù)、相互繼承權(quán)利等相關(guān)財(cái)產(chǎn)制度才契合婚姻家庭關(guān)系的本質(zhì)。夫妻雙方可以約定分別財(cái)產(chǎn)制;此外,夫妻財(cái)產(chǎn)一般屬于共有財(cái)產(chǎn)。雖然這兩種財(cái)產(chǎn)制度均可以用所有權(quán)制度進(jìn)行解釋,但單純運(yùn)用所有權(quán)思路設(shè)計(jì)夫妻財(cái)產(chǎn)制度,則無法實(shí)現(xiàn)其應(yīng)有功能。
三、市民社會(huì)共同體中的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與財(cái)產(chǎn)配置
私法的個(gè)人主義傾向往往忽略市民社會(huì)共同體的存在,但私法中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總是處于社會(huì)共同體之中,私法財(cái)產(chǎn)秩序需要放到社會(huì)共同體中考察。
1.市民社會(huì)共同體中通過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形成財(cái)產(chǎn)秩序
近代以來的私法理論習(xí)慣從“人身-財(cái)產(chǎn)”對(duì)立的角度出發(fā)解釋社會(huì)關(guān)系,以致曲解了財(cái)產(chǎn)對(duì)生活的從屬性質(zhì):強(qiáng)調(diào)身份法制度規(guī)則的倫理性,忽視身份法制度規(guī)則的技術(shù)性;注重從技術(shù)角度規(guī)范財(cái)產(chǎn)的歸屬與流轉(zhuǎn),忽視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中倫理價(jià)值的滲透。雖然學(xué)界已經(jīng)開始從人格角度研究人身與財(cái)產(chǎn)之間的關(guān)系,認(rèn)識(shí)到財(cái)產(chǎn)總是人的財(cái)產(chǎn),但人格不是人身與財(cái)產(chǎn)之間真正的聯(lián)結(jié)點(diǎn)。因?yàn)槿烁袷浅橄蟮模c財(cái)產(chǎn)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持較為純粹的倫理性,人格制度不能直接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難以溝通人身與財(cái)產(chǎn)之間的關(guān)系。身份作為一項(xiàng)社會(huì)組織技術(shù),本身就有“利益份額”的含義,多數(shù)情形中表現(xiàn)為財(cái)產(chǎn)份額。因此,在社會(huì)共同體中需要通過身份調(diào)整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以獲得財(cái)產(chǎn)秩序與社會(huì)秩序。
2.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配置財(cái)產(chǎn)的基本形式
在分配領(lǐng)域,身份意味著利益份額,身份差異意味著利益份額的差異。現(xiàn)代社會(huì)中一般存在三次分配,每次分配中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均發(fā)揮不可替代的功能,每一種分配關(guān)系中貫徹不同的身份政策。
第一次分配通過市場(chǎng)機(jī)制完成,財(cái)產(chǎn)分配的身份政策注重效率。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發(fā)揮基礎(chǔ)作用,注重資源配置效率,不同身份可以獲得不同的財(cái)產(chǎn)份額。第一次分配主要通過企業(yè)機(jī)制實(shí)現(xiàn),在企業(yè)內(nèi)部,主要依據(jù)當(dāng)事人在企業(yè)身份體系中不同的身份位置配置不同的利益份額。投資者、經(jīng)營(yíng)者、勞動(dòng)者因?yàn)椴煌纳矸荻鴱钠髽I(yè)中獲得不同的利益配置,投資者享有利潤(rùn),經(jīng)營(yíng)者享有工資與業(yè)績(jī)報(bào)酬,勞動(dòng)者獲得工資。在第一次分配中,強(qiáng)者通過優(yōu)勢(shì)身份,獲得大份額的利益,通過身份差異的財(cái)產(chǎn)分配鼓勵(lì)競(jìng)爭(zhēng),以促進(jìn)社會(huì)財(cái)富的增加。同時(shí),這種身份財(cái)產(chǎn)政策導(dǎo)致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造成財(cái)富的兩極分化,從經(jīng)濟(jì)上塑造并強(qiáng)化了人們的身份差異,從而影響社會(huì)公平。
第二次分配通過政府機(jī)制完成,財(cái)產(chǎn)分配的身份政策注重公平。從社會(huì)成員的不同經(jīng)濟(jì)條件所造就的不同身份狀況出發(fā),通過稅收調(diào)節(jié)高收入者的收入,通過福利補(bǔ)償?shù)褪杖胝摺T诂F(xiàn)代社會(huì),政府機(jī)制已經(jīng)滲透于市場(chǎng)內(nèi)部,政府福利制度發(fā)揮著彌補(bǔ)市場(chǎng)機(jī)制缺陷的功能,人們?nèi)粘I罾娴囊徊糠謥碓从谡峁┑母@U鞫愂菄?guó)家從社會(huì)中獲得財(cái)富的主要方式,稅收關(guān)系具有公法屬性,但稅收的征納活動(dòng)同樣具有私法意義。在民法上,國(guó)家可以成為一個(gè)獨(dú)立的所有權(quán)主體,居民也是獨(dú)立的所有權(quán)主體,征稅意味著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從居民手中轉(zhuǎn)移到國(guó)家手中。在稅收制度中,居民身份就是一種連接制度,居民負(fù)有納稅的義務(wù),是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據(jù)。在所得稅的起征點(diǎn)制度中,通過設(shè)置起征點(diǎn),將居民進(jìn)行分類區(qū)別對(duì)待,確定納稅與否;而累進(jìn)稅率制度將不同收入水平者進(jìn)行區(qū)別對(duì)待,以確定征稅的比例。
在福利制度中,公民身份是政府福利與個(gè)人生活的聯(lián)結(jié)機(jī)制,公民身份是享受社會(huì)福利的基本依據(jù)。現(xiàn)代國(guó)家對(duì)公民的基本生存負(fù)有責(zé)任,政府應(yīng)該保障公民達(dá)到符合文明性的最低生活標(biāo)準(zhǔn),公民普遍享有基本福利,低收入身份群體還享受社會(huì)救濟(jì)。在具體的制度設(shè)計(jì)上是設(shè)立貧困線,收入水平?jīng)]有達(dá)到貧困線的人,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第三次分配通過社會(huì)捐助等機(jī)制完成,財(cái)產(chǎn)分配的身份政策注重良知,體現(xiàn)為對(duì)財(cái)富上的強(qiáng)勢(shì)身份群體配置捐助義務(wù)。財(cái)富的集中使財(cái)富的擁有者成為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多元權(quán)力中心之一,富豪與財(cái)團(tuán)決定著社會(huì)公眾的衣食住行的方式,發(fā)揮著類似于政府一樣的影響力。因此,基于這種社會(huì)勢(shì)力的不對(duì)稱性,富豪群體既然能夠影響公眾的生活就應(yīng)該對(duì)公眾承擔(dān)信義義務(wù)。在美國(guó)等發(fā)達(dá)國(guó)家,富豪回報(bào)社會(huì)已經(jīng)成為默示規(guī)則。例如,比爾·蓋茨于2008年6月表示將捐出580億美元資產(chǎn)。[16]有理論認(rèn)為獲得和占有財(cái)富本身不能證明其正當(dāng)性。“那些認(rèn)為他 ‘造就了’他自己和他的生意的產(chǎn)業(yè)組織者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在他手邊的全部社會(huì)制度都是預(yù)備好了的,如技術(shù)工人、機(jī)器、市場(chǎng)、治安與秩序——這些大量的機(jī)構(gòu)與周邊的氛圍,是千百萬人與數(shù)十代人共同創(chuàng)造的結(jié)果……我們不應(yīng)當(dāng)說甲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創(chuàng)造了若干財(cái)富,乙創(chuàng)造了若干財(cái)富,而應(yīng)當(dāng)說利用和借助現(xiàn)存的社會(huì)制度,財(cái)富的增加屬于甲者比屬于乙者較多或較少。”[17]西方學(xué)者提出了財(cái)產(chǎn)的信托理論,認(rèn)為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富豪并非僅僅為了個(gè)人和家族擁有財(cái)產(chǎn),而是為社會(huì)管理和使用財(cái)產(chǎn),其地位相當(dāng)于社會(huì)財(cái)產(chǎn)的受托人。[18]這種理論一方面闡述了私人財(cái)產(chǎn)的社會(huì)性,另一方面也為富豪身份群體承擔(dān)社會(huì)捐助道義責(zé)任提供法理依據(jù)。在社會(huì)行為方面就應(yīng)該通過捐助機(jī)制實(shí)現(xiàn)利益平衡,緩和社會(huì)矛盾,維護(hù)社會(huì)秩序。同樣,對(duì)接受捐助的弱勢(shì)群體也并非接受施舍,在道義上無須處于劣勢(shì),接受捐助也是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一種基本生活方式。
四、企業(yè)中的身份權(quán)力秩序和財(cái)產(chǎn)秩序
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身份體系是為組織生產(chǎn)活動(dòng)而構(gòu)造的,主要通過身份秩序整合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通過身份權(quán)力規(guī)范企業(yè)財(cái)產(chǎn)支配關(guān)系。
1.企業(yè)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身份調(diào)整的基礎(chǔ)
企業(yè)是人們進(jìn)行生產(chǎn)協(xié)作的組織形式,身份安排是實(shí)現(xiàn)這種社會(huì)化協(xié)作的基本手段,物權(quán)與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結(jié)合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才能有效規(guī)范企業(yè)財(cái)產(chǎn)秩序。在企業(yè)中,以企業(yè)家的管理代替市場(chǎng)中的契約調(diào)整機(jī)制,將科學(xué)技術(shù)、人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dòng)力和財(cái)產(chǎn)整合為一體,形成具有經(jīng)營(yíng)能力的市場(chǎng)主體,這種整合依賴大量的身份關(guān)系紐帶。企業(yè)形成一種身份共同體,進(jìn)入企業(yè)的成員獲得特定的身份崗位,通過身份職權(quán)安排支配相應(yīng)的財(cái)產(chǎn)和人力資源份額。由此,人力資源與財(cái)產(chǎn)得以整合,形成企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能力。
企業(yè)身份體系按照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要求塑造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通過身份秩序安排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秩序。企業(yè)財(cái)產(chǎn)直接滿足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需要,按照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特定環(huán)節(jié)的需要進(jìn)行安排,企業(yè)中的財(cái)產(chǎn)總是處于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特定環(huán)節(jié)、具備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特定功能并受到特定身份權(quán)力支配。單項(xiàng)財(cái)產(chǎn)進(jìn)入企業(yè)組織,按照企業(yè)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需要嵌入生產(chǎn)程序,形成與企業(yè)結(jié)構(gòu)功能相應(yīng)的組合資產(chǎn),在組合資產(chǎn)的基礎(chǔ)上形成營(yíng)業(yè)功能體。企業(yè)通過身份體系協(xié)調(diào)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運(yùn)用身份權(quán)力主導(dǎo)財(cái)產(chǎn)運(yùn)行,支配特定的財(cái)產(chǎn)運(yùn)行和他人行為。
2.企業(yè)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身份調(diào)整的制度支柱
(1)企業(yè)的主體身份和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一旦登記獲得法律人格,企業(yè)就獲得營(yíng)業(yè)主體身份,取資者成為交易相對(duì)方打交道的對(duì)象。這種營(yíng)業(yè)體身份使其財(cái)產(chǎn)相應(yīng)地轉(zhuǎn)化為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在商事關(guān)系中通過連續(xù)的、有計(jì)劃的、同種類的營(yíng)業(yè)活動(dòng)創(chuàng)造利潤(rùn)。
與企業(yè)的獨(dú)立主體身份相適應(yīng),企業(yè)財(cái)產(chǎn)作為一個(gè)整體歸屬于企業(yè)。在有些法律關(guān)系中,企業(yè)財(cái)產(chǎn)會(huì)超越其具體結(jié)構(gòu),而被當(dāng)作一項(xiàng)整體財(cái)產(chǎn)對(duì)待。例如,在歸屬關(guān)系上,德國(guó)法將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視為集合物;在流轉(zhuǎn)關(guān)系上,各國(guó)商法規(guī)定在營(yíng)業(yè)轉(zhuǎn)讓中以營(yíng)業(yè)為交易單位。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中的每個(gè)單項(xiàng)的資產(chǎn)都可以獨(dú)立出來,用物權(quán)、債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表示,并進(jìn)行單獨(dú)轉(zhuǎn)讓。但是,這些財(cái)產(chǎn)如果處于獨(dú)立形態(tài)就不是營(yíng)業(yè)財(cái)產(chǎn)。“這些資產(chǎn)要素必須結(jié)合為有機(jī)的整體,才具有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的屬性。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有時(shí)表現(xiàn)為企業(yè)的整體,但有時(shí)表現(xiàn)為企業(yè)的某個(gè)系統(tǒng)、某項(xiàng)業(yè)務(wù)或者某些營(yíng)業(yè),如公司的某個(gè)店面或者某個(gè)車間。”[19]
(2)投資者、經(jīng)營(yíng)者身份權(quán)力區(qū)分和財(cái)產(chǎn)二重性。市場(chǎng)運(yùn)行中的經(jīng)營(yíng)權(quán)離不開所有權(quán)。為了方便經(jīng)營(yíng),投資者將自己的所有權(quán)轉(zhuǎn)讓給企業(yè),在企業(yè)的名義下實(shí)現(xiàn)所有權(quán)與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統(tǒng)一。在企業(yè)制度內(nèi)部,財(cái)產(chǎn)的使用價(jià)值與價(jià)值形態(tài)實(shí)現(xiàn)分離,投資者與經(jīng)營(yíng)者權(quán)力分別依附于財(cái)產(chǎn)的價(jià)值與使用價(jià)值形態(tài)。
投資者享有終極意義上的所有權(quán),其身份權(quán)力依附于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形態(tài)。舍棄財(cái)產(chǎn)具體形態(tài),經(jīng)過抽象實(shí)現(xiàn)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化,通過同質(zhì)的貨幣予以衡量;再經(jīng)過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從價(jià)值上將其劃分為標(biāo)準(zhǔn)化的等額股份,結(jié)合證券表現(xiàn)投資者的股權(quán)。這樣,價(jià)值形態(tài)的財(cái)產(chǎn)就處于投資者支配之下。
經(jīng)營(yíng)者享有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經(jīng)營(yíng)權(quán)依附于財(cái)產(chǎn)的使用價(jià)值形態(tài)。經(jīng)營(yíng)者作為企業(yè)的經(jīng)營(yíng)機(jī)關(guān),通過職權(quán)實(shí)現(xiàn)對(duì)企業(yè)財(cái)產(chǎn)的支配。只有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行使才能帶來價(jià)值的增值,因此企業(yè)財(cái)產(chǎn)的使用價(jià)值形態(tài)置于經(jīng)營(yíng)者支配之下。
(3)企業(yè)身份權(quán)力的差序結(jié)構(gòu)和信義義務(wù)。不同身份職位依據(jù)職權(quán)支配不同的人力與財(cái)產(chǎn)資源,形成企業(yè)身份權(quán)力的差序結(jié)構(gòu)。掌握經(jīng)營(yíng)決策權(quán)的董事和經(jīng)理、掌握監(jiān)督權(quán)的監(jiān)事和掌握實(shí)際控制權(quán)的大股東成為身份強(qiáng)權(quán)者。為保護(hù)投資者利益,公司法引進(jìn)信義義務(wù),確認(rèn)企業(yè)身份強(qiáng)權(quán)者與其他利害關(guān)系人之間的信義關(guān)系,[20]要求受信人對(duì)受益人或委托人負(fù)有信義義務(wù)。
3.企業(yè)身份體系和財(cái)產(chǎn)安排
企業(yè)通過身份體系整合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每一種身份對(duì)財(cái)產(chǎn)均具有支配意義和分配意義。
(1)企業(yè)內(nèi)部的基本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從實(shí)物形態(tài)考察,企業(yè)資產(chǎn)分為有形資產(chǎn)和無形資產(chǎn)。[21]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的組織優(yōu)化程度、經(jīng)營(yíng)者的經(jīng)營(yíng)能力、企業(yè)在行業(yè)競(jìng)爭(zhēng)中所處的位置、主營(yíng)業(yè)務(wù)在市場(chǎng)中的產(chǎn)業(yè)周期、甚至是政府的相關(guān)扶持政策等因素卻是企業(yè)的無形財(cái)產(chǎn)。企業(yè)內(nèi)部的財(cái)產(chǎn)存在于組織安排狀態(tài)之中,單項(xiàng)財(cái)產(chǎn)嵌入整體財(cái)產(chǎn),每一項(xiàng)具體的財(cái)產(chǎn)均被鎖定在既定的位置上,形成專用性財(cái)產(chǎn),發(fā)揮預(yù)定的功能。在企業(yè)內(nèi)部,關(guān)注財(cái)產(chǎn)的物理性質(zhì)、結(jié)構(gòu)與財(cái)產(chǎn)組合的整體功能,以滿足企業(yè)運(yùn)行的要求,一般不會(huì)獨(dú)立考察某項(xiàng)財(cái)產(chǎn)的價(jià)值與使用價(jià)值。因此,單項(xiàng)財(cái)產(chǎn)往往喪失通用性,市場(chǎng)流通能力下降,在市場(chǎng)中單獨(dú)變現(xiàn)出現(xiàn)障礙或者易于發(fā)生價(jià)值流失。從價(jià)值形態(tài)觀察,財(cái)產(chǎn)在企業(yè)外部表現(xiàn)為進(jìn)入企業(yè)的投資,流出企業(yè)的利潤(rùn)、工資、稅收;財(cái)產(chǎn)在企業(yè)內(nèi)部表現(xiàn)為企業(yè)總資產(chǎn)。這些價(jià)值形態(tài)的資產(chǎn)同樣處于特定功能狀態(tài)。
(2)企業(yè)內(nèi)部的基本身份體系。只有人才能支配財(cái)產(chǎn)的運(yùn)行。在企業(yè)制度設(shè)計(jì)中,人的意志與專業(yè)的市場(chǎng)能力被客體化,通過身份設(shè)計(jì)整合進(jìn)財(cái)產(chǎn)組合體中,從而使企業(yè)財(cái)產(chǎn)演變?yōu)閮?nèi)化了人的創(chuàng)造性的財(cái)產(chǎn)。正是身份崗位體系的安排,將人的稟賦依據(jù)不同生產(chǎn)需要置于不同的崗位,行使不同的身份權(quán)力,從不同環(huán)節(jié)支配不同的財(cái)產(chǎn)份額。企業(yè)通過股東、董事、監(jiān)事、經(jīng)理、職工身份崗位和職權(quán)安排實(shí)現(xiàn)企業(yè)運(yùn)作。企業(yè)身份體系負(fù)載了企業(yè)權(quán)利和權(quán)力體系。企業(yè)身份體系主要包括:1)投資者身份。通過股東身份,在投資者個(gè)人與企業(yè)之間建立聯(lián)系,股東的身份權(quán)包括財(cái)產(chǎn)收益權(quán)與治理權(quán)。前者是從企業(yè)獲得紅利的權(quán)利,持股比例是分配比例的依據(jù)。后者是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決策與控制的權(quán)力,企業(yè)通過設(shè)立股東會(huì)和股東身份崗位將投資人的意志引進(jìn)企業(yè),投資者的營(yíng)利愿望轉(zhuǎn)化為企業(yè)機(jī)關(guān)的職能,通過股東會(huì)權(quán)力和股東權(quán)的行使將股東的謀利要求轉(zhuǎn)變?yōu)槠髽I(yè)運(yùn)行的動(dòng)力。2)經(jīng)營(yíng)者身份。企業(yè)通過設(shè)置董事、經(jīng)理身份崗位,將職業(yè)經(jīng)營(yíng)者的商業(yè)能力整合于財(cái)產(chǎn)中,將經(jīng)營(yíng)者的商業(yè)才能轉(zhuǎn)變?yōu)槠髽I(yè)的經(jīng)營(yíng)能力,使企業(yè)具備市場(chǎng)運(yùn)營(yíng)能力。3)監(jiān)督者身份。監(jiān)事身份崗位將股東的監(jiān)督權(quán)日常化、內(nèi)部化。監(jiān)事權(quán)力的行使對(duì)象是經(jīng)營(yíng)者的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力,通過身份權(quán)力制衡以防止經(jīng)營(yíng)者濫用身份權(quán)力。4)勞動(dòng)者身份。企業(yè)通過職工身份將勞動(dòng)者的勞動(dòng)與財(cái)產(chǎn)結(jié)合于生產(chǎn)過程中,勞動(dòng)者的勞動(dòng)技能與生產(chǎn)過程的特定環(huán)節(jié)相結(jié)合。勞動(dòng)者在企業(yè)身份權(quán)力體系中處于受支配地位,接受經(jīng)營(yíng)者的管理、監(jiān)督。
(3)企業(yè)內(nèi)部身份的財(cái)產(chǎn)意義。投資者身份的直接意義是財(cái)產(chǎn)支配權(quán)。投資者轉(zhuǎn)化為股東,通過股東會(huì)行使決策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對(duì)企業(yè)財(cái)產(chǎn)運(yùn)用具有最高支配權(quán)。投資者身份的最終意義在于決定財(cái)產(chǎn)利益歸屬。投資者擁有企業(yè)的剩余財(cái)產(chǎn)索取權(quán),企業(yè)財(cái)產(chǎn)運(yùn)作過程是其資產(chǎn)以社會(huì)化運(yùn)作方式循環(huán)與增值(也可能虧損)的過程。
經(jīng)營(yíng)者身份的財(cái)產(chǎn)意義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1)在于企業(yè)財(cái)產(chǎn)支配權(quán),即經(jīng)營(yíng)者在職權(quán)范圍內(nèi)按照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目標(biāo)支配人力要素與物質(zhì)要素;(2)經(jīng)營(yíng)者既是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指揮者,其本身的經(jīng)營(yíng)管理能力也為企業(yè)營(yíng)業(yè)財(cái)產(chǎn)所內(nèi)化,成為企業(yè)的一種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3)獲得薪金報(bào)酬。
五、家庭中的身份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安排
人類基本生活共同體是家庭,其外部擴(kuò)展為家族。農(nóng)村的村社、城市的社區(qū)均屬于生活共同體。在這些領(lǐng)域存在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而形成的。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按照人們生活需要規(guī)范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形成相應(yīng)的財(cái)產(chǎn)配置和流轉(zhuǎn)規(guī)則。為行文方便,以下集中從家庭關(guān)系進(jìn)行分析。
1.家庭內(nèi)部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調(diào)整的基本規(guī)則
在生活共同體中,個(gè)人之間存在著年齡、性別、能力、健康狀況、社會(huì)地位、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異,也存在血緣、婚姻等身份聯(lián)系,從而形成相互協(xié)作關(guān)系。在這個(gè)生活共同體中,一些人有能力從市場(chǎng)中獲得財(cái)產(chǎn),另一些人沒有能力從市場(chǎng)中獲得財(cái)產(chǎn);通過身份關(guān)系,弱者依賴強(qiáng)者,強(qiáng)者扶助弱者。生活共同體的財(cái)產(chǎn)是為了滿足其成員的生活需要而存在的:在歸屬關(guān)系中,財(cái)產(chǎn)的獨(dú)占性被突破,實(shí)質(zhì)上已并非純粹私的所有;生活共同體內(nèi)部財(cái)產(chǎn)流轉(zhuǎn)突破了等價(jià)有償規(guī)則,遵循相互扶助的身份調(diào)整規(guī)則。生活共同體中的財(cái)產(chǎn)秩序服從于倫理秩序,法律依據(jù)特定身份關(guān)系設(shè)定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和財(cái)產(chǎn)義務(wù),如未成年人對(duì)父母支付生活費(fèi)的請(qǐng)求權(quán),夫妻之間的扶助義務(wù)。
2.身份關(guān)聯(lián)與人格獨(dú)立之間的財(cái)產(chǎn)利益衡平
現(xiàn)代私法對(duì)生活共同體內(nèi)部身份關(guān)系進(jìn)行調(diào)整的關(guān)鍵是如何從財(cái)產(chǎn)上衡平身份關(guān)聯(lián)與人格獨(dú)立。首先,生活共同體中的財(cái)產(chǎn)是為了滿足倫理秩序需要,財(cái)產(chǎn)制度設(shè)計(jì)必須體現(xiàn)并服務(wù)于特定身份關(guān)系。以婚姻家庭為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婚姻法》(以下簡(jiǎn)稱《婚姻法》)第17條規(guī)定的共有財(cái)產(chǎn)制度支持夫妻之間的共同生活關(guān)系,在穩(wěn)定的兩性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形成共同的生活消費(fèi)單位,承擔(dān)種族的繁衍功能并實(shí)現(xiàn)養(yǎng)老育幼的社會(huì)功能。其次,在身份關(guān)系之中,個(gè)人人格仍然存在,個(gè)人財(cái)產(chǎn)仍有意義。婚姻并非像血緣聯(lián)系那樣由先天注定,而是后天通過身份行為創(chuàng)設(shè)、變更和解除,與人格獨(dú)立相伴的意志自由和財(cái)產(chǎn)獨(dú)立仍有意義。根據(jù)2001年修訂的《婚姻法》第18、19條的規(guī)定,約定財(cái)產(chǎn)制有三種形式:一般共同制、部分共同制和分別財(cái)產(chǎn)制。法律為當(dāng)事人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多種模式,擴(kuò)大了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圍。其背后的邏輯是強(qiáng)化個(gè)人獨(dú)立性與獨(dú)立的財(cái)產(chǎn)利益保護(hù),與私法中以獨(dú)立、抽象、均質(zhì)的個(gè)人為規(guī)范對(duì)象的邏輯相一致。但是,這種變化趨勢(shì)也存在可商榷之處,我們不能忽視夫妻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是在夫妻身份關(guān)系內(nèi)部存在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具有特定的身份功能,因而只能滿足常態(tài)婚姻家庭內(nèi)部關(guān)系對(duì)利益的需要。[22]現(xiàn)在,婚姻家庭領(lǐng)域的個(gè)人獨(dú)立有過度膨脹的傾向,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通過遺囑將全部的遺產(chǎn)遺贈(zèng)給保姆而導(dǎo)致沒有任何過錯(cuò)的法定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落空并且該遺囑得到法院支持的事件。[23]
如何在財(cái)產(chǎn)制度規(guī)則上做出適當(dāng)?shù)陌才乓院馄交橐黾彝ブ械纳矸萋?lián)系與人格獨(dú)立?我們有必要借鑒法國(guó)法、瑞士法上的特留份制度。特留份是法律所強(qiáng)制規(guī)定的繼承人應(yīng)該享有的最低限度的繼承財(cái)產(chǎn)份額。特留份制度重在保護(hù)婚姻家庭中的倫理秩序,為財(cái)產(chǎn)繼承中的倫理身份關(guān)系份額設(shè)置了底線,賦予法律強(qiáng)制力,限制了當(dāng)事人意志自由。有反對(duì)者認(rèn)為特留份制度會(huì)導(dǎo)致不勞而獲,坐食遺產(chǎn)的依賴心理,有損社會(huì)公平和效率,主張加以限制。[24]筆者認(rèn)為,問題關(guān)鍵在于如何協(xié)調(diào)個(gè)人自由意志與身份約束之間的關(guān)系。一些國(guó)家的民法排除特留份制度,將家庭財(cái)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依據(jù)交易邏輯歸屬于個(gè)人,這種個(gè)人是抽象的原子化的個(gè)人,而非身份關(guān)系中的個(gè)人,這種財(cái)產(chǎn)也被認(rèn)為是抽象同質(zhì)性的財(cái)產(chǎn),而非為了家庭生活而存在的目的性、功能性財(cái)產(chǎn)。這樣一來,財(cái)產(chǎn)脫離了身份關(guān)系約束,所有權(quán)人的自由意志出現(xiàn)膨脹。既然繼承關(guān)系本性是身份關(guān)系,既然人生活在婚姻家庭制度之中,通過身份聯(lián)系授受財(cái)產(chǎn)利益是人們的生活的常態(tài),那么無視身份約束的個(gè)人對(duì)所有權(quán)的意志自由就損害了婚姻家庭身份關(guān)系的固有功能。因此,法律應(yīng)當(dāng)限制被繼承人的處分權(quán),維護(hù)法定繼承制度及親屬之間的身份關(guān)系,不至于使繼承人突然失去生活來源。
六、個(gè)人身份和無形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形成
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人身與財(cái)產(chǎn)之間的關(guān)系出現(xiàn)新的趨向,個(gè)人身份開始具有財(cái)產(chǎn)意義,優(yōu)勢(shì)身份在市場(chǎng)評(píng)價(jià)中演變?yōu)闊o形財(cái)產(chǎn)權(quán)。
1.個(gè)人身份的財(cái)產(chǎn)意義
有學(xué)者開始注意人身關(guān)系的財(cái)產(chǎn)意義。德國(guó)法學(xué)家施瓦布認(rèn)為:“人的人格發(fā)展和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經(jīng)濟(jì)財(cái)產(chǎn),人就不能生存;人所能支配的經(jīng)濟(jì)財(cái)產(chǎn)越少,生存機(jī)會(huì)也越小,人格權(quán)的實(shí)質(zhì)內(nèi)容也就越少。人在相當(dāng)可觀的程度上恰恰是通過其財(cái)產(chǎn)而獲得發(fā)展,最明顯的是通過擁有消費(fèi)品而獲得發(fā)展。”[25]19世紀(jì)法國(guó)的兩位學(xué)者奧布里和羅闡述了廣義財(cái)產(chǎn)理論,認(rèn)為廣義財(cái)產(chǎn)無區(qū)別地包括一切財(cái)產(chǎn),尤其是天賦財(cái)產(chǎn)。[26]廣義財(cái)產(chǎn)除了包括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的權(quán)利之外,還包括人格權(quán)利。該理論將抽象的整體性財(cái)產(chǎn)與人格合為一體,揭示了人格與財(cái)產(chǎn)的統(tǒng)一性,將個(gè)人擁有的抽象意義上的全部財(cái)產(chǎn)視為其人格自有之物。[27]近年我國(guó)學(xué)者認(rèn)識(shí)到人格中包含有倫理要素和財(cái)產(chǎn)要素,自然人的血液、乳汁等衍生物以及身體器官均可以具有交換價(jià)值;姓名、肖像等標(biāo)表型人格可以轉(zhuǎn)化為商業(yè)利益并在市場(chǎng)中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因?yàn)槿烁駲?quán)商品化的客觀現(xiàn)實(shí),我們必須承認(rèn)人格權(quán)的財(cái)產(chǎn)性,人格利益已經(jīng)包括精神利益和財(cái)產(chǎn)利益。”[28]
其實(shí),相對(duì)于人格而言,身份與財(cái)產(chǎn)之間具有更為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性。身份關(guān)系與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之間往往相互滲透、互相支持,身份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無形財(cái)產(chǎn)權(quán)。法國(guó)有學(xué)者在研究人格物、商事人格權(quán)等問題時(shí)已經(jīng)觸及身份財(cái)產(chǎn)權(quán),明確區(qū)分將肖像“視為人的固有組成部分”與“視為可以利用的財(cái)產(chǎn)”在法律意義上的不同,指出前者主要適用于普通人領(lǐng)域,旨在阻卻他人的擅自利用;而后者則主要適用于“名人”領(lǐng)域,旨在賦予該名人利用(或者不利用)其肖像以取得商業(yè)利益的自由。[29]“視為人的固有組成部分”對(duì)應(yīng)人格,而“視為可以利用的財(cái)產(chǎn)”則對(duì)應(yīng)身份。在人格標(biāo)志的商業(yè)化領(lǐng)域,只有運(yùn)用人格和身份兩種機(jī)制才能解讀這種無形財(cái)產(chǎn)利益的形成與運(yùn)作,人格獨(dú)立是這種無形財(cái)產(chǎn)利益的歸屬機(jī)制,身份差異是這種無形財(cái)產(chǎn)的形成機(jī)制。人格功能僅僅體現(xiàn)為突出某個(gè)特定人可以作為商業(yè)評(píng)價(jià)對(duì)象,將優(yōu)勢(shì)身份所產(chǎn)生的財(cái)產(chǎn)利益和精神利益歸屬于某個(gè)主體。只有身份才能夠?qū)⑦@個(gè)人的價(jià)值在市場(chǎng)結(jié)構(gòu)中予以衡量確定。雖然人人具有各種各樣的身份,每種身份或多或少地具有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但能夠具有突出市場(chǎng)效應(yīng)和商業(yè)價(jià)值的只會(huì)是那些擁有優(yōu)勢(shì)身份的人。
2.優(yōu)勢(shì)身份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的形成
我們從財(cái)產(chǎn)角度考察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個(gè)人之間的身份差異可以通過財(cái)產(chǎn)體現(xiàn),擁有優(yōu)勢(shì)身份的名人擁有更大份額的無形財(cái)產(chǎn)資源。這是身份差異而非人格平等所產(chǎn)生的社會(huì)效應(yīng)。例如,財(cái)富媒體《福布斯》公布,2008年籃球運(yùn)動(dòng)員姚明的總收入達(dá)到了5 200萬美元。[30]姚明為什么具有如此高的商業(yè)價(jià)值?如果運(yùn)用人格理論是無法解釋的,因?yàn)槿巳司哂腥烁瘢渌藶楹尾荒芡ㄟ^廣告代言獲得收入?真正的原因在于姚明的超級(jí)球星身份,人們能夠?qū)χa(chǎn)生健康、力量等積極方面的聯(lián)想。因此,商家請(qǐng)姚明代言,就能夠使產(chǎn)品得到消費(fèi)者的追捧,從而提高市場(chǎng)占有率,帶來更高的利潤(rùn)。由此觀之,政治明星、文體明星這些優(yōu)勢(shì)身份均能夠誘導(dǎo)消費(fèi)者的消費(fèi)行為,從而形成市場(chǎng)價(jià)值。而對(duì)法人來說,商譽(yù)是一種有關(guān)法人的商業(yè)或職業(yè)道德、資信、商品質(zhì)量和服務(wù)質(zhì)量方面的評(píng)價(jià)。[31]這種評(píng)價(jià)導(dǎo)致了不同企業(yè)之間的差異,形成了知名品牌等優(yōu)勢(shì)身份企業(yè)。這些企業(yè)的名牌優(yōu)勢(shì)身份意味著其擁有穩(wěn)定的客戶資源,獲得了一個(gè)有組織的市場(chǎng),產(chǎn)品和服務(wù)價(jià)格會(huì)明顯高于同類產(chǎn)品和服務(wù),從而形成市場(chǎng)價(jià)值。
3.優(yōu)勢(shì)身份的無形財(cái)產(chǎn)權(quán)屬性
在市場(chǎng)領(lǐng)域,不同身份獲得不同的市場(chǎng)評(píng)價(jià),實(shí)現(xiàn)了身份要素的財(cái)產(chǎn)化。此時(shí),身份之“份”直接體現(xiàn)為財(cái)產(chǎn)份額,優(yōu)勢(shì)身份則產(chǎn)生大份額的財(cái)產(chǎn)利益,身份權(quán)在有些情景中表現(xiàn)為單純的無形財(cái)產(chǎn)權(quán)。德國(guó)學(xué)者耶林從羅馬法出發(fā),區(qū)分了有體物與無體物,認(rèn)為名譽(yù)、榮譽(yù)等利益屬于無形財(cái)產(chǎn)。[32]另外,肖像、姓名、聲音等人格權(quán)標(biāo)志都可能具有巨大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其價(jià)值大小一般取決于個(gè)人在公眾中的知名度和聲望。知名人士可以允許將公眾對(duì)他的關(guān)注以及與此相聯(lián)系的、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進(jìn)行商業(yè)化,將自己的肖像、姓名或者具有識(shí)別功能的其他人格標(biāo)志用于商品和服務(wù)的廣告以獲取報(bào)酬。可見,姓名、肖像的價(jià)值形成于市場(chǎng)評(píng)價(jià),依據(jù)不同身份產(chǎn)生不同數(shù)量的無形財(cái)產(chǎn)。就名人而言,身份資源意味著取得財(cái)產(chǎn)的可能性,只有通過市場(chǎng)行為才可以轉(zhuǎn)化為實(shí)在財(cái)產(chǎn)。需要指出的是,對(duì)演藝公司等企業(yè)而言,擁有明星的質(zhì)量和數(shù)量則屬于人力資本范疇,構(gòu)成其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
在司法領(lǐng)域,法院已經(jīng)開始將優(yōu)勢(shì)身份作為無形財(cái)產(chǎn)對(duì)待,提供財(cái)產(chǎn)法方式保護(hù),認(rèn)為未經(jīng)本人允許而對(duì)其人格標(biāo)志進(jìn)行商業(yè)化利用的廣告,其侵害對(duì)象主要不是精神利益,更多表現(xiàn)為當(dāng)事人商業(yè)利益。這時(shí),當(dāng)事人所感受的名譽(yù)和聲望受到的傷害,要比經(jīng)濟(jì)上的損害小得多。[33]在侵犯肖像權(quán)的案件中,不同身份者請(qǐng)求賠償?shù)臄?shù)額也各不相同。在英美法中,這種無形財(cái)產(chǎn)權(quán)通過判例加以確認(rèn)。1953年,美國(guó)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法官弗蘭克在“海蘭案”中不再將商業(yè)性地使用他人的身份局限在精神痛苦的范圍之內(nèi),而是將其作為一種財(cái)產(chǎn)權(quán)侵害,[34]從判例上確認(rèn)了名人真正需要保護(hù)的是其身份上的商業(yè)利益。對(duì)人格標(biāo)志非法商業(yè)化案件的裁判,采用身份法技術(shù)具有明顯優(yōu)勢(shì)。因?yàn)槿绻麖木窭娼嵌冗M(jìn)行保護(hù),必然離不開人格權(quán)邏輯,囿于人格平等,理論上只能對(duì)同類侵權(quán)判決標(biāo)準(zhǔn)化的賠償額,無法就不同身份的受害人判決不同的賠償數(shù)額。如果從身份利益角度進(jìn)行保護(hù),可以依據(jù)身份邏輯,就不同身份的受害人判決不同的賠償數(shù)額。因?yàn)樯矸荽嬖诓町悾煌矸菡叩娜烁駱?biāo)志上負(fù)載的商業(yè)利益不同,權(quán)利人損失的可得財(cái)產(chǎn)利益同樣也存在差異。
注釋:
[1]參見[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闖譯,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
[2]參見薛軍:《法律行為理論:影響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重要因素》,《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3]參見謝懷栻:《民法總則講要》,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頁。
[4]私法中的身份是指?jìng)€(gè)人在市民社會(huì)關(guān)系中具有私法意義的定位與相應(yīng)的利益份額,是身份關(guān)系為私法所規(guī)制的結(jié)果。
[5]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財(cái)產(chǎn)運(yùn)用主要依賴公司、證券、銀行、信托等商事制度,身份調(diào)整機(jī)制在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例如,法律為交易中的經(jīng)營(yíng)者與消費(fèi)者配置不同的權(quán)利義務(wù)。
[6]身份體是指進(jìn)行身份安排的組織單位,如家庭、社團(tuán)、社區(qū)等;身份體是介于個(gè)人與市民社會(huì)的中間層次。
[7]《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4頁。
[8]傳統(tǒng)民法設(shè)計(jì)出以人格權(quá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互為參照系的二元結(jié)構(gòu)。其局限性在于,僅僅從人格權(quán)角度觀察人倫秩序,人為地舍棄了身份領(lǐng)域;其實(shí),人格關(guān)系與身份關(guān)系均屬于人身關(guān)系,人格制度規(guī)則與身份制度規(guī)則均規(guī)范人倫秩序。
[9]因?yàn)楣蓶|可以進(jìn)入企業(yè)內(nèi)部機(jī)構(gòu),通過股東大會(huì)行使重大事項(xiàng)決策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和人事任免權(quán),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司事務(wù);而債權(quán)人始終是公司外部人,無法影響公司事務(wù)。
[10]參見[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xué)原理——權(quán)利的科學(xué)》,沈叔平譯,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版,第48頁。
[11][德]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范揚(yáng)、張企泰譯,商務(wù)印書館1961年版,第46頁。
[12][13]參見[德]卡爾拉倫茨:《德國(guó)民法通論》,王嘵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頁。
[14]這種“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說法在第一個(gè)層次上體現(xiàn)的是人與自然關(guān)系中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diǎn)。其實(shí),在自然界中,野獸也可以捕獲人作為食物,人可以對(duì)象化;人作為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同樣需要為生存而努力,為生存而付出代價(jià),并非天生就是目的。在第二個(gè)層次上體現(xiàn)的是社會(huì)關(guān)系中的人格尊嚴(yán)與人人平等觀點(diǎn)。但問題是,在實(shí)際的社會(huì)生活中,不受約束支配的獨(dú)立、自由、平等是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的,受支配同樣是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常態(tài)。
[15]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頁。
[16]參見孫琎:《蓋茨本周退體 580億美元捐慈善》,《第一財(cái)經(jīng)日?qǐng)?bào)》2008年6月24日。
[17][英]倫納德霍布豪斯:《社會(huì)正義要素》,孔兆政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頁。
[18]參見資中筠:《財(cái)富的歸宿:美國(guó)現(xiàn)行公益基金述評(píng)》,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88頁。
[19][21]參見葉林:《營(yíng)業(yè)資產(chǎn)法律制度研究》,《甘肅政法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7年第1期。
[20]信義關(guān)系是指特定當(dāng)事人之間的一種不對(duì)等的法律關(guān)系,即受信人處于一種優(yōu)勢(shì)地位,而受益人或委托人處于弱勢(shì)地位,受信人作為權(quán)力擁有者,有權(quán)以其行為改變他人的法律地位,而受益人或委托人則必須承受這種被改變的法律地位且無法對(duì)受信人直接控制。
[22]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cái)產(chǎn)分割問題的若干意見》第10條的規(guī)定注重保護(hù)夫妻身份關(guān)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個(gè)人財(cái)產(chǎn)自由。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9條的規(guī)定體現(xiàn)了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獨(dú)立的傾向,而淡化了夫妻身份聯(lián)系的身份財(cái)產(chǎn)屬性。這反映出一種錯(cuò)誤的傾向。
[23]參見仲民等:《杭州小保姆贏得百萬遺產(chǎn)》,《北京晨報(bào)》2001年1月21日。
[24]參見章禮強(qiáng):《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行繼承法遺囑自由過度的反思》,《現(xiàn)代法學(xué)》2004年第1期。
[25][德]迪特爾施瓦布:《民法導(dǎo)論》,鄭沖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頁。
[26][27]參見尹田:《無財(cái)產(chǎn)即無人格》,《法學(xué)家》2004年第2期。
[28]袁雪石:《論人格權(quán)的二元性》,博士學(xué)位論文,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法學(xué)院,2007年,第2頁。
[29]轉(zhuǎn)引自馬俊駒、張翔:《人格權(quán)的理論基礎(chǔ)及其立法體例》,《法學(xué)研究》2004年第6期。
[30]參見張婧:《姚明年收入力壓科比詹姆斯 中國(guó)巨人成NBA首富》,《東方早報(bào)》2009年9月7日。
[31]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頁。
[32]參見王利明:《人格權(quán)法研究》,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