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29 17:44:28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chuàng)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王維作品,希望這些內(nèi)容能成為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jìn)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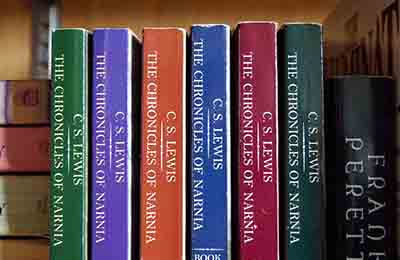
寫作背景:安定統(tǒng)一的盛唐社會。
王維的鳥鳴澗,作于開元年間游歷江南之時,此詩是王維題友人皇甫岳所居的云溪別墅所寫的組詩皇甫岳云溪雜題五首的第一首,是詩人寓居在今紹興縣東南五云溪的作品。 據(jù)新唐書王維傳記載,王維于開元初進(jìn)士及第后授太樂丞,因坐伶人舞黃獅事被貶為濟(jì)州同倉參軍,直到開元二十三年張九齡執(zhí)政才返京任右拾遺。王維漫游若耶,觸景生情,聯(lián)想到前人描寫若耶溪的名句,欲與古人爭勝厘毫,出藍(lán)而勝藍(lán),于是有了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這一聯(lián)以動寫靜的精彩詩句。從鳥鳴澗詩體現(xiàn)的風(fēng)格和意境分析,此詩應(yīng)作于唐玄宗開元盛世時期,為王維青年時代的作品。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一、三原色與補(bǔ)色關(guān)系的運(yùn)用
三原色的運(yùn)用是繪畫的基礎(chǔ),王維的詩中隨時可見悅目的三原色。《桃源行》中前四句:“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yuǎn),行盡青溪忽值人。”“漁舟”的原木色“黃”,水的“白”,桃花、紅樹的“紅”,青溪的“藍(lán)”,不正是紅、黃藍(lán)三原色的體現(xiàn),再加上春的綠,“古津”和遠(yuǎn)山的紫灰色的調(diào)和,從而形成了一張柔和亮麗色彩豐富的“油畫作品”。“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這首詩同樣也運(yùn)用了三原色和白色,給我們描繪了一張冷色調(diào),色彩豐富統(tǒng)一諧調(diào)的風(fēng)景人物畫作品。
西方色彩科學(xué)中另一種色彩關(guān)系即補(bǔ)色關(guān)系在王維詩中也隨處可見。補(bǔ)色具有強(qiáng)烈的對比效果,任何一對互補(bǔ)色既對立又統(tǒng)一,可以將充實圓滿軟化為對立面的平衡。當(dāng)它們對比時能突出相互的鮮明性,當(dāng)他們混合時,又相互消除,變成一種灰黑色。互補(bǔ)色中的互補(bǔ)因子構(gòu)成了一個簡明的結(jié)構(gòu)整體,因此,其在色彩中具有一種獨(dú)特的表現(xiàn)力。王維《高原》詩中“桃花復(fù)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積雨輞川作》中“雨中草色綠湛染,水上桃花紅欲燃。”這都體現(xiàn)了詩人早已感知到了補(bǔ)色運(yùn)用的藝術(shù)魅力。詩人對補(bǔ)色運(yùn)用不是牽強(qiáng)粗俗的,而是深入研究后從科學(xué)的角度進(jìn)行的描繪。
二、冷和暖的對比
與此同時,王維詩歌還揭示了色彩學(xué)的另一規(guī)律:冷和暖的對比。冷暖是色彩組成的重要因素,沒有冷暖對比的繪畫作品就可以說是沒有色彩。有了冷暖的對比可以產(chǎn)生空間效果,暖色有前進(jìn),擴(kuò)張感,冷色有后退,收縮感;正確處理好冷暖關(guān)系,可以表達(dá)出自然界的真實色彩和空間關(guān)系。“紅豆生南國,春來發(fā)幾枝。” “桃紅復(fù)含春雨,柳綠更帶朝煙。” “雨中草色綠湛染,水上桃花紅欲燃。” “綠艷閑且靜,紅衣淺復(fù)深。”這些同樣都可以說是冷暖對比在詩中的運(yùn)用。
色彩純度和明度的對比在王維詩中也有所體現(xiàn)。“漠漠水田飛白鷺的,陰陰夏木囀黃鸝”便是使用了色彩純度的對比,使“水田”與“白鷺”,“夏木”與“黃鸝”相互映襯把積雨的輞川山野描寫的畫意盎然。水田的綠,夏木的綠在雨天中都蒙上了一層迷茫的灰色,降低了色彩的純度,從而使得白鷺更白,黃鸝更黃,使白黃的色彩純度更高,形成了色彩純度、明度上的對比。“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fù)下”,秋雨中的小瀑布和淺淺的溪水天然形成一片霧色,落下水滴激起白色的水花,驚起旁邊的白鷺從霧色中跳出;這里是空間,更是明度的對比。“桃紅復(fù)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嫩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同樣也是降低了色彩的純度,從而形成了補(bǔ)色低純度的合理安排。白色運(yùn)用的重要性在這里也被充分體現(xiàn)。白色的明度最高,無色相。漠漠、陰陰、秋雨、跳波、宿雨、朝煙、新粉這些都象征著白色,都起到降低顏相和純度,提高色彩明度作用。
三、環(huán)境色的應(yīng)用
王維的詩中環(huán)境色的運(yùn)用也是常見的,環(huán)境色的應(yīng)用,不僅增強(qiáng)了畫面之間色彩的呼應(yīng)和聯(lián)系,還豐富了畫面色彩。“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蒼苔上人衣來是環(huán)境色的影響,在光線的照射下,坐在蒼苔邊的人受蒼苔反射綠色的影響,綠光波映到人身上而產(chǎn)生的感覺。而山林的翠綠的色彩把人的衣衫都滲透了,這種環(huán)境色的影響可以使人忘記衣服固有的色彩。“渭城朝雨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就更絕了,詩人不再用什么“欲上”、“濕”,直接說“客舍”為“青青”,表現(xiàn)出“柳色”對“客舍”之色的影響。
環(huán)境色對物體影響越大,物體的固有色就越弱。但物體正面始終是受光源色影響的。沒有光,就沒有色彩,就是一個黑暗的世界。色彩的產(chǎn)生是依靠光源的,光線的冷暖也就是決定著物體受光面的色調(diào)。光線的冷暖就是我們所說的光源色。落日余暉和藍(lán)天白云下的同一物體受光面所呈現(xiàn)的色彩必然是不同的。而月光更是色彩的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者。王維就用了冷暖不同的光源,把自己的詩照耀的五彩斑斕或皎潔無暇。“行人返深巷,積雪帶余暉”,白色的雪因光線光波的影響而戴上了落日的橙色。“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等,都體現(xiàn)了詩人對這些光色影響的運(yùn)用。沒有山月,就沒有澗芳之色襲人衣,沒有朱燈也不會有麗服之色映顏;而“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更直接道出沒有月光就不能見清泉流于石上的光色原理。“返影入深林,復(fù)照青苔上”同樣也反映了光照的原理,同時還道出了物體不僅有受光還有暗部和投影的原理。
四、五行觀念的影響
王維的近體詩占他所有詩的三分之二,這些詩表現(xiàn)出了詩人的最高水平。這在學(xué)術(shù)界已是公論。而其中的一些或清新或壯麗的小詩多為詩人最具代表的作品,像《山居秋暝》、《終南山》、《過香積寺》、《漢江臨眺》、《使至塞上》等,在這里有潺潺的小泉,也有壯闊的江河,更有滋潤萬物的雨。跟同是以山水詩聞名的孟浩然相比,他出現(xiàn)水意象的詩不過是總數(shù)的百分之二七,還不到三分之一。然而正是這不到三分之一的詩奠定了王維繼李杜后又一位大家的地位。這些為數(shù)不多的詩句中一半多都“濕意”盎然。可以說,水意象在王維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水意象有著深刻的淵源,在先秦文學(xué)里即被賦予了豐富的內(nèi)涵,詩人要在這上面出彩是件不容易的事。這一點(diǎn)上,王維無疑做得很成功。他的“水”跟前代和同時代的山水詩人有什么不同?從風(fēng)格上看,摩詰善于將水與光搭檔,將詩境刻畫的真可謂“水月鏡花,不可湊泊”。如“寒燈坐高館,秋雨聞疏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秋日光能澹,寒川波自翻”等。謝靈運(yùn)非常著名的詩句如“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王維一改謝靈運(yùn)詩的麗,將“白”等清淡之色融入詩中,洗凈鉛華,多了幾分空靈之趣。如此善用“光”自然和他的畫家身份分不開,一種顏色的深淺往往和光的投射有關(guān),畫家對色彩十分敏感,能分辨出主要是光的影響。
從水意象蘊(yùn)含的取用上看,王維詩中的水意象可大致分為這幾類:第一,借水來表現(xiàn)禪思;例如,“安知清流轉(zhuǎn),偶與前山通”、“長風(fēng)萬里來,江海蕩煩濁”、“喬木萬馀株,清流貫其中。前臨大川口,豁達(dá)來長風(fēng)”、“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等。前幾句他借用流水意象喻指佛法的滌神蕩性的功能,最后一句用長長的江河水比喻佛法的博大精深,因為佛理的深奧,所以不可講,不可說,正所謂佛訓(xùn)之“不立文字”,只好用這類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詩語來表達(dá)。
第二,借水意象表現(xiàn)對離人、故鄉(xiāng)的思念之情,禪宗傳燈錄有一相當(dāng)出名的公案:老僧三十年前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后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體歇處,依然是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老僧的三種境界對應(yīng)的是三種觀物方式,這一類便是語錄中第二階段。例如,“五湖千萬里,況復(fù)五湖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欲歸江淼淼,未到草凄凄”、“檣帶城烏去,江連暮雨愁”、“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蕩槳向臨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等。這類詩作在多愁善感的詩人的作品中隨處可見。上文說過,以水喻情的傳統(tǒng)如詩經(jīng)自古有之。這樣以水長比喻情誼的深長的例子我們能找到很多。王維是個重情義的詩人,第一句寫他與思念的對象相隔千里,“水”成為他們會面的阻力;第二句將“水”擬人化,人愁雨也愁;第三句將“春色”擬人化,似乎離別之情只借春色表現(xiàn),然而春色看不見摸不著,只有垂柳和綠水代春天訴說對離人的眷戀;這類詩歌在近體詩中偏多,成就遠(yuǎn)遠(yuǎn)高于第一類詩。
第三,水意象和其他意象一起給讀者營造一個自洽自足的世界,它們不表現(xiàn)別的,只表現(xiàn)它們自己。第三階段“可以說是對自然現(xiàn)象‘即物即真’的感悟,對山水自然自主的原始存在做無條件的認(rèn)可,這個信念同時要我們摒棄語言和心智活動而歸回本樣的物象”。而王維很多名詩就是在這種觀物方式下寫成的,那么其中的水意象即水本身,但是這已經(jīng)不同于自然萬物中的水了,例如“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春池深且廣,會待輕舟回。靡靡綠萍合,垂楊掃復(fù)開”、“輕舸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dāng)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fù)下”、“木末芙蓉花,山中發(fā)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等。它們集中在他的近體詩中,屬于詩人一些最經(jīng)典的作品。立威廉說:“王維的詩,景物自然興發(fā)與演出,作者不宜主觀的情緒或知性的邏輯介入去擾亂眼前景物內(nèi)在生命生長與變化的姿態(tài)。”我們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這些詩里通常看不到主人公,主人公不是詩人自己,也不是某一個特定的人,或者一個群體,他表現(xiàn)的山水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而是一種具有無我、普遍性意義的山水,甚至在這些山水詩中消融了時間性――表現(xiàn)春夜,表現(xiàn)山林,并不是某個時間上一點(diǎn)的春夜山林。而水意象作為一個獨(dú)立的審美意象,全賴于眾意象的“和鳴”,它們共同發(fā)聲,方能有一首完整和諧的詩譜出。到達(dá)了這個意義層面上的“水”,反過來,又需要直觀悟境,在詩學(xué)領(lǐng)域中又可稱為“詩性直觀”,即對外物作即物即真的感應(yīng),在此過程中,容不得任何妄想,禪語曰:“諸和尚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詩人和“水”為代表的自然物已消融為一體,中間已抹去了不必要的介質(zhì)。
而前面兩類水意象的寓意取用遠(yuǎn)遠(yuǎn)沒有達(dá)到第三類普遍性,只停留在見山第二階段,即“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水意象在這里成為了抒發(fā)離情、講喻佛法的工具,那么詩人和自然之間始終是隔的,對立的。吳言生說:見山第二階段是一種認(rèn)識哲學(xué)思維,“這個活動就逐漸離開新鮮直抒的山水,而移入概念世界,去尋求意義和聯(lián)系”。因此,這類詩是有我的,有時間的,具體的,甚至是有對象的。例如“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蕩槳向臨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這是這類詩中較出色的句子,它發(fā)生在一個楊柳依依的春天,詩人的朋友要遠(yuǎn)行了,詩人站在渡頭遙望著舟上朋友漸行漸遠(yuǎn)的身影。詩人在這里把對朋友的眷戀之情比喻為“春色”,春色無窮無盡,那么“我”對“你”的眷戀也像春色一樣,這里賦予了“春色”一種動態(tài),從而使“春色”人情化了。這里的“水”說到底是感性的。
第三類詩代表了王維詩作的最高水平。考察王維的這類詩作,我們發(fā)現(xiàn)水意象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雖然被譽(yù)為山水詩作的壓軸之作,但其中水意象的頻繁出現(xiàn)多于山意象,事實上“山水詩”中的“山水”指的是泛化的“山水”,即客觀的自然界。這決不是偶然。王潤華在《王維詩學(xué)》中抽繹出王維詩的主題:桃源。他說,《王左丞集》中卷首詩即是《桃源行》,另有八首桃源行詩作,王維往往是通過無心無意的桃源旅程而是詩歌達(dá)到與山水不分彼此的詩學(xué)境界,這種桃源之旅首先就是要窮涉水源了。事實上,陶淵明筆下的武陵人進(jìn)入桃源的唯一途徑便是蕩水行舟了。“水”成為通往仙境桃源的關(guān)鍵,那這里可不可以說,王維對“水”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他喜愛追逐水源,“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可以說,王維是一個極善于描摹“水”姿態(tài)的詩人,從水的形態(tài)上來講,有川、有江、有河、有溪、有泉、有澗、有池;從水的顏色上看,有碧的、有青的;從水的透明度上看大多都是清的、澄的;從水的情態(tài)上講有動的和靜態(tài)的、動態(tài)的有縱向流動、也有橫向流動;更有靜態(tài)水,有孤獨(dú)的,也有自洽自足的;從意象的搭配上來看,多跟光、山、云、林、月、蓮、渡頭、舟聯(lián)系在一起。王維的是因為有“水”的加入顯得更加澄凈、活潑通透,也因為水的明凈剔透而賦予了部分詩歌空靈、清靜無塵的意境。“智者要山,仁者樂水”,因為有水的存在,詩化了詩人的心;反過來也正是因為詩人喜愛“水”,才能更富感情更深刻地呈現(xiàn)水意象的本來面目。(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xué)人文院)
參考文獻(xiàn):
[1]陳鐵民,[M]王維論稿,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6.
[2]聞一多,王蒙等[M]唐詩二十講,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3]吳言生[M]禪宗詩歌境界,北京:中華書局,2002.
關(guān)鍵詞:山水精神;自然水墨畫境
水墨的出現(xiàn),是藝術(shù)家向自然本質(zhì)的追求。限制技巧的不在于技巧本身,而是人對藝術(shù)提出要求的“藝術(shù)意欲”。換句話說,自魏晉以來到盛唐,作品的最大容納者是朝廷、貴族和寺院,這三者所要求的是神佛人物,而不是山水,于是,技巧上當(dāng)然向神佛人物方面發(fā)展,而非向山水方面來發(fā)展。和山水畫在六朝產(chǎn)生的情況有所不同,水墨形式有它自身的魅力。中國山水畫之所以以水墨為統(tǒng)宗,這是和山水畫得以成立的中國藝術(shù)精神思想的背景和這種背景所形成的性格密切關(guān)聯(lián)在了一起,而并不是說青綠色不美。但本質(zhì)與現(xiàn)象,在中國的思想中并不是對立的,所以說水墨和著色也不是對立的。順著水墨的意味而著色時,那么所著色的自然為淡彩,或水墨與淡彩并用。因為水墨與淡彩并不是對立的,所以,一位畫家,有主向的不同,而在水墨和著色之間,都盡可以自由的運(yùn)用。
宗炳、王微,他兩人在藝術(shù)的精神上,直接的奠定了山水畫的基礎(chǔ)。隋朝展子虔的“亦長遠(yuǎn)近山川,咫尺千里”,這可能暗示山水畫到了隋代有了進(jìn)展。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中開始記錄有不少的山水畫家以及他們的作品,但此時還沒有將山水、松石、樹木分列門類,這也就說明了山與林、林與泉,即一般的所謂的“山林”、“林泉之勝”的統(tǒng)一概念還沒有真正形成,因而在作品中也還沒有能夠得到融合。而這一融合,大概也是經(jīng)過中唐一直到五代,才在不知不覺之中逐漸完成的。
張彥遠(yuǎn)在《歷代名畫錄》中的主要著眼點(diǎn),是由前輩畫家們的畫法所給予的山水畫的影響而言的,并沒有人的師承的意味。從這一點(diǎn)來說以張彥遠(yuǎn)的山水之變始于吳道子的說法為最可信的理論根據(jù)。所以他在卷中描述吳道子:“因?qū)懯竦郎剿紕?chuàng)山水之體,自為一家。”山水畫法,到了吳道子而一變的“變”,是山水畫在長期停頓狀態(tài)中開始走向完成性的發(fā)展的變。不過,張彥遠(yuǎn)又說“山水之變,始于吳,成于二李”。山水藝術(shù)在作品之中的初步完成,一直要到李思訓(xùn)才完成,這似乎是有關(guān)技巧上的問題。正如荊浩的《筆法記》中所說的,吳道子“有筆而無墨”,無墨,也就是不容易表現(xiàn)山水的量塊和陰陽向背,山水的形貌不完整。李思訓(xùn)、李昭道父子,以金碧青綠山水入畫。不僅是為了色澤的更美,而實際上也是為了后來的皴染的發(fā)展彌補(bǔ)了上面說的缺點(diǎn),我們也可以說,山水藝術(shù)的精神啟發(fā)于宗炳、王微,其形體則是完成于李思訓(xùn)。李思訓(xùn)之后,我們開始有了真正值得成為山水藝術(shù)的作品。
王維與張?,都略晚于李思訓(xùn)而成為同時代的人物。荊浩說“王右丞筆墨宛麗,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真思”,這也就說明王維是以水墨代青綠。不過,當(dāng)時的所謂水墨,并不完全是排斥色彩的,而是將青綠變?yōu)榱说省<兯嫵霈F(xiàn)的時間,推斷為晚唐。此后,水墨和水墨兼淡彩,成為中國山水畫的顏色的主干,這是來自山水畫的基本的性格。
從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來看,水墨山水畫的一個源頭是繪畫筆法的變化,我們可以在吳道子的一系列繪畫中看到的側(cè)鋒轉(zhuǎn)筆的立體感,他疏放的筆法,應(yīng)用在山水樹石上也很有意義。吳道子的實際意義是把《游春圖》上那種勾勒山石樹木的筆法解放了出來。所以,在他的筆下,連景物都換發(fā)了生命。這是水墨能夠逐漸從設(shè)色畫中獨(dú)立出來的重要轉(zhuǎn)折。在這個轉(zhuǎn)折點(diǎn)上,王維出現(xiàn)的意義非同小可。王維山水的詩境以清新自然為尚,因此,對于“水暈?zāi)隆碧貏e的能發(fā)揮其所長。后代推崇王維,而不是中晚唐的表現(xiàn)派風(fēng)格的水墨畫家,強(qiáng)調(diào)的就是這種意境。
王維生活在8世紀(jì)初至中葉,是一位才智出眾的藝術(shù)家。他工詩善畫,精通音律,在當(dāng)時享有盛譽(yù)。他的詩以表現(xiàn)山水為主,早年有一些描寫邊塞的詩篇,氣勢遼闊,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就是膾炙人口的名句,他詩中的繪畫般的意境,尤其受人稱道。在文人畫壇上,王維的詩境成為畫家要表現(xiàn)的最高理想。那么,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為,從王維開始,繪畫的功能在逐漸的轉(zhuǎn)變著,從面對公眾服務(wù)政教,轉(zhuǎn)向面對自我。服務(wù)于個人和心靈。王維將其落實在山水境界中。也就是說,六朝的宗炳、王微雖然從理論上認(rèn)識到山水的意義,但由于那時的山水畫還并沒有成為完全獨(dú)立的學(xué)科,所以,人們也就很難從畫面上體會到山水精神的妙處了。
以山水風(fēng)格而論,王維被推為水墨一端的主要開創(chuàng)人,是和他對青綠山水的認(rèn)識和變通連在一起的,因為他同時擅長青綠和水墨兩種形式的山水風(fēng)格。從北宋中后期開始,文人畫家和鑒賞家們特別的看重了他的這些方面,也帶動了文人畫思潮的泛濫。
在立意上,王維最讓后人感興趣的是《袁安臥雪圖》。畫中描繪的是東漢寒士袁安的故事。袁安在大雪過后,寧愿忍餓受凍,也不像其他人那樣去官府申請救濟(jì)。后來,因為郡首路過門前,深深地為他高尚的人格所感動,就將他作為楷模向世人宣揚(yáng)。但畫家卻在雪地上添了數(shù)枝芭蕉,引起了宋人的熱烈討論。從地理上講,北方洛陽的雪景中,怎么會可能出現(xiàn)嶺南才有的芭蕉呢?再從季節(jié)上講,芭蕉也不在冬天生長。按照寫實的觀點(diǎn),王維的作品有悖于物理常形。可是,從畫家參修的禪理來看,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可以超越物象本身。芭蕉作為參禪的話頭,出現(xiàn)在雪景之中,則更加的能夠傳達(dá)出畫中的主題,也就是表現(xiàn)袁安的高尚人格。這種跨越時空局限的視覺創(chuàng)造,對唐代日趨成熟的再現(xiàn)性作品來說,無疑的是一種革命。作為“詩佛”的王維,他信仰的是佛教禪學(xué)的境界,往往有一種不可言傳之妙。這幅畫早已不存在了,但他對后來的文人畫創(chuàng)作,的確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王維留給后人的遺產(chǎn),在境界上超過了吳道子的“口訣”、“畫樣”。恰恰相反的是,王維在達(dá)到“畫中有詩”的過程中也發(fā)展了水墨山水的表現(xiàn)手法,這也是從北宋開始文人畫家們之所以推崇王維的主要原因。王維的水墨風(fēng)格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特點(diǎn),連文獻(xiàn)的記載也語焉不詳。可是,在他生活的時代的確形成了一種氣氛,使我們能夠感受其中的要義。
將水墨山水藝術(shù)單獨(dú)提出來介紹,是要強(qiáng)調(diào)水墨的形式在中國繪畫中的特殊性。它從書法的用筆發(fā)展而來,不但改變了人物畫的造型語言,而且?guī)恿酥袊嫷拇笞兏铩氖⑻频街刑茣r期對墨法的認(rèn)識和實驗中,可以注意到“潑墨”、“破墨”的形式在達(dá)到個性表現(xiàn)方面的巨大潛力。但是,在這些實驗中,有許多極端的例子離開了用筆的“骨法”,因此流于疏野狂放,引起了另外一些畫家們的注意。五代時北方山水畫家的代表人物荊浩就將“筆”、“墨”作為一對概念提出,創(chuàng)造了有筆有墨的山水表現(xiàn)程式“皴法”。在這樣的程式基礎(chǔ)上,他進(jìn)一步概括了山水畫的基本認(rèn)識范疇,即“思”和“景”的關(guān)系,為后來的中國畫壇主流指明了總的發(fā)展藝術(shù)方向。中國藝術(shù)中的風(fēng)格和自然的關(guān)系,開始變得一目了然。和北方的全景山水相對應(yīng)的是江南的全景山水,也出現(xiàn)在南唐畫家董源、巨然的筆下,他們“淡抹青嵐成一體”的趣味特點(diǎn),在北宋中后期成了文人畫家推崇的風(fēng)格,并在元中后期全面的得到了發(fā)展,在畫史上有極其深遠(yuǎn)的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洪再新.中國美術(shù)史[M].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4:7991.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此詩簡短20字,但從后人對其賞析的熱衷度,以及其對王維對詩歌語言掌控力之大手筆的體現(xiàn)程度而言,此詩可謂是王維神靜氣閑之時,難得的短而精、師道自然、出類拔萃卻難以復(fù)制的代表之作。
我們講,知人而論世,從詩歌作品的賞鑒角度來說,詩人的作品寫出時間、身世、地位、居住地等與之相關(guān)的背景和作品的賞鑒的是否契合作者的初衷(談不上正誤之分),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自然,這首五言絕句的背景也是值得推敲、斟酌。王維幼年即聰慧,少有慧根,也在早年就樹立了大鵬展翅的政治抱負(fù)。但后來值政局變化無常而逐漸消沉下來,吃齋念佛。四十多歲的時候,他特地在長安東南的藍(lán)田縣輞川營造了別墅,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鳥鳴澗》這首詩是他隱居生活中的一個篇章。于是我們很容易的把“詩言志”的聯(lián)想附加到此首詩之中。自然,我認(rèn)為也是如此。
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筆者認(rèn)為,發(fā)于情、郁于思而為文、成章,或清閑,或幽憤,或感懷,或憑吊,或中肯,或遲疑。詩歌亦如此。雖然說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宏論,在當(dāng)時以及后代引起極大的反響,但是我們知道,詩歌作為文學(xué)作品,最終由人而作,也是為人而作,當(dāng)然更多的是為己而作。總之,文學(xué)最終要?dú)w結(jié)為人的情感起伏得失。并不是說要懷疑白居易大詩人的文學(xué)觀點(diǎn),只是說詩歌作為文學(xué),并非只單單是為時、為事而文學(xué),為文學(xué)而文學(xué)。從筆者來看,這是狹隘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理念,也必將限定了文學(xué)的表達(dá)、表現(xiàn)的外延,存在著方向性的問題。
于是,拋開上述落窠臼的話,我們會更明澈清晰的理解,這首詩為著一個飽滿但凄清的“閑靜”而作。
而從詩歌內(nèi)容角度來講,此詩全詩圍繞著一個夜景而展開。前兩聯(lián)“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開篇便點(diǎn)情,一“閑”字而人之狀態(tài)全出。詩人無事清幽,欣賞著夜色清寂。身邊的桂花慵懶飄落,極其細(xì)致入微。而此時,大境界里,山澗也如人清幽,不摻半分嘈雜和市儈。情與景的契合、交融、相互映襯,只突出了兩個字“閑”“靜”,卻給人唏噓低回,意味深長之意。后兩句“月出”“驚”“時鳴”三個動態(tài)之詞,以動而襯靜,便更是渲染了這一刻的靜謐空幽。這一聯(lián)一經(jīng)補(bǔ)上。全詩的境界則更上了一個層次。自然,我們不能忽視的還有該詩的意象的選擇,“人”“桂花”“夜”“春山”“月”“山鳥”“春澗”等一起發(fā)力,渲染出了一種難言卻可心領(lǐng)神會的生氣、意蘊(yùn)。
雖然全詩未明言自己的身心靜思,但從這20個字我們可以明顯且不可遏抑的感覺到,其作品的主要內(nèi)容,詩人自身遠(yuǎn)離紅塵,隱居不仕的愿望。
從詩歌的構(gòu)思角度來講,其可圈可點(diǎn)之處也是隨處盡現(xiàn)。“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這是一句古語,古來好詩都是就天成好景,用妙手記敘出來。故此而言,幾經(jīng)雕琢、穿鑿之痕深重的作品倒顯得意味尋常,讀來也沒有如此的意蘊(yùn),與作者凈心擯氣,閑心空思,在浮華纏繞,人情匆匆的現(xiàn)代社會,尋得佳時,共享得這一片刻的歡愉和升華。詩句雖是人刻意為之,但是此詩之中寫景并不顯刻意鋪陳,意境自然,如同信手拈來一般。我們由此便可明曉其詩的構(gòu)思之精妙,詩借自然,而出亦如自然,這是一種絕高的藝術(shù)境界。
從文學(xué)理論角度來講,文學(xué)接受者也是文學(xué)完成價值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從此而言,文學(xué)作品的價值經(jīng)讀者的閱讀環(huán)節(jié)的完成而得以實現(xiàn)。在現(xiàn)代社會的難以逃避的浮華喧囂里,人情匆匆,詩情也匆匆,好像任何事都生了翅膀,再也慢不下來。一句“慢慢走,欣賞啊”成為多數(shù)人再也難以企及的奢望。只是愿在中夜,缺月如,人靜氣閑之時,執(zhí)一卷詩,特別是王維的詩,雖不穿越時間,抵至那方唯漫堂皇的舞臺,但心如此,情如此,與時代的高華崇思相互擊節(jié)應(yīng)和,與詩人共同體味那一抹“人靜山空,徑稀紅落”之景,之靜,之凈,之境。
關(guān)鍵詞:王維 山水詩 空靈 生命
義務(wù)教育階段的語文課程中,王維作品入選不算太多,但其詩文尤其是山水田園詩以其精致的描繪筆法,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高雅的審美情趣,對提升學(xué)生的文化品位,促進(jìn)學(xué)生的精神成長不容小覷。王維鐘愛文學(xué),精通音樂,擅長繪畫,精研佛理。他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踵事增華,學(xué)陶之自然渾成,取謝之細(xì)麗精工,在描寫自然山水的詩歌里,以曠逸恬淡、清新脫俗的風(fēng)格,創(chuàng)造出一種“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禪”的空靈明秀的獨(dú)特詩境。
王維仕途沉浮坎坷,飽經(jīng)磨難,他能從世俗生活中體會宗教情感,在“空”與“靜”的審美境界中獲得啟悟,從而使個體生命能擺脫世俗的羈絆與困厄,完成了超越現(xiàn)實的大建構(gòu),走向了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我。
一.空明境界中的生命萌動
佛教強(qiáng)調(diào)有中悟空,幻中解空。所謂現(xiàn)實世界所有表象皆是幻象,本質(zhì)終歸為空。空幻觀留給王維的藝術(shù)觀是豐富的,深刻的。在眾多的詩篇中,他甚至以“空”字直接入詩:
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 ――《山居秋暝》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鹿柴》
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過香積寺》
暮云空磧時驅(qū)馬,秋日平原好射雕。 ――《出塞作》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 ――《積雨輞川莊作》
獨(dú)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 ――《秋夜獨(dú)坐》
來者復(fù)為誰,空悲昔人有。 ――《孟城坳》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山中》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 ――《酬張少府》
實象非象,透過紛繁復(fù)雜的表象,探索到事物空幻的本質(zhì),并從中形成生命之流,是王維詩歌的一種基調(diào)。
以《終南山》為例:“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這是一首出色的山水詩,詩人以濃重的筆墨描繪了朝暈夕陰、氣象萬千的終南諸峰。首聯(lián)先從地理形勢說起,夸張地寫出了鐘南山的形長勢壯。“近天都”“到海隅”極言終南山的磅礴氣勢,勾勒出了一個極為廣闊的空間。在這寥廓的空間里山勢跌宕拓展,從象內(nèi)延伸到象外,猶如一股無形的生命之流,綿延千里。緊接著,作者描繪如此廣廓的空間里那似是而非、瞬間幻變的風(fēng)云。回首是云,前瞻是霧;乍看似有,駐足卻無。通過白云、青靄的飄渺輕盈表現(xiàn)出生命氣韻的生動,并以云霧之高遠(yuǎn)潔凈來寄托詩人對理想境界的向往與追求。即使日出之后云霧消散,終南山恢復(fù)其本來面目,那本來面目依然是變換萬端,捉摸不定。這就使得這山多了一份空靈,添了一份含蓄。由此推之,在這廣袤的時空里,來去匆匆的過程永遠(yuǎn)沒有終極的意義。如此來看,生命就是一個不斷擴(kuò)展的過程。尾聯(lián)以問宿作結(jié),仍與山的高大關(guān)聯(lián)。既寫出了山的雄渾,亦寫出了山的變化,更有人物的活動。在這里,詩人完成了無形的生命氣韻向有形的生命實體的回歸。詩歌就此戛然而止,生命重又遁入無形之中。至此,詩人有限的生命向無限的生命延伸,達(dá)到了有限與無限的統(tǒng)一,并使得詩人的主體性在追求永恒的本體價值存在的同時,在空明、飄動、清靜、恬淡的境界中,獲得了充分的闡釋與萌發(fā)。
二.靜謐意象中的生命永恒
王維早年究心佛理,受到北禪宗影響,晚年又接近南禪宗,這使他個人內(nèi)心進(jìn)入一種自我冥合的無我之境。他喜歡獨(dú)坐時感悟,將禪的靜空與山水審美體驗合而為一,在對山水的描寫中反映出一種清幽的禪趣。他更善于以動寫靜,喧中求寂,超于物外,達(dá)到心境的靜謐。“靜”構(gòu)成了王維詩歌意境的另一個重要意念,它也是佛家的一個特定范疇。佛教以“寂”作為真理的本體,在瞬間領(lǐng)悟永恒的虛空,用靜寂之心去觀照萬物靜寂的本質(zhì)。由是觀之,王維最后的精神歸宿是透過自然界的生生不息,萬象常新,領(lǐng)悟到其本質(zhì)的最終的靜寂。
王維《鳥鳴澗》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本詩描述了月夜鳥鳴春澗的幽美境界,取得了以動襯靜的藝術(shù)效果。能體驗到桂花的飄落,這是怎樣的一種靜!無言的月出驚醒沉睡的山鳥,一個“驚”字,那又是怎樣的一種喧!然而,禪的本質(zhì)終究是指向靜謐的,詩人無論怎樣渲染動態(tài)聲響,卻始終追尋空寂的境界。正如釋慧皎在《高僧傳》中所說:“禪世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這一思維方式,以“妙萬物”為內(nèi)核,以“寂”為基本途徑。其基本特征在于緣法察境,唯寂乃明,猶如淵池魚石,心澄而悟,則可凝照一切,妙觀萬物。
無論是桂花飄落,鳥鳴聲聲,都只在瞬間。瞬間過后,便歸于永恒的靜滅。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靜謐的觀照和飛躍的生命構(gòu)成藝術(shù)的兩元,也是禪的心靈狀態(tài)。
王維的作品常常選擇大自然中最能表現(xiàn)寧靜清曠的景物作為素材,諸如明月、白云、幽谷、蒼松、大漠孤煙、遠(yuǎn)山野水、荒村古寺等等。看起來一切都是動的,但他所傳達(dá)出來的意味,卻是永恒的靜,本體的靜。在動中體驗極靜,在實景中獲得虛境,在紛繁的表象中獲得本體,在本體中合而為一,從而在瞬間的直感領(lǐng)域中獲得生命的永恒。自然界之花開花落,鳥鳴深澗,雨綠月明,然而就是在這對自然的片刻頓悟中,讓人感受到的卻是那不朽的生命存在,從人事轉(zhuǎn)向自然,再從自然轉(zhuǎn)向空寂,從而獲得一種徹底的精神解脫。
三.沖淡情趣中的生命勃發(fā)
禪悟是非理智的直覺體驗,沒有情緒的沖動,追求的是一種絕不激動、平靜淡泊的心境。在這種非理智的直覺體驗中,將人生的各種悲歡離合、七情六欲引向空無的永恒,化為心靈深處的對物欲情感的淡泊。因此,“空”和“靜”的靜默觀照,必然帶來真正的審美趣味的平淡,從而形成特別沖淡的韻味,并在這種沖淡的純審美的情趣中凸顯人的主體性。記得一位哲人說過:“在某種高峰體驗中,人與世界相同一而無特定的情感。”王維詩歌所追求的正是這種無特定情感的最高體驗,在這體驗中卻又暗含了詩人積極的主體價值訴求。
以《終南別業(yè)》為例:“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dú)往,勝事空自知。偶然值林叟,談笑無返期。”這是一首描繪詩境的詩,也是描繪人生的詩,更是充滿禪機(jī)妙悟的詩。寫景,敘情,皆似信手拈來,好不著力,可謂平淡自然之至。它所展現(xiàn)的正是沖和淡雅,清新自然的詩風(fēng)。在無心無念之中,似乎接近了佛性的神秘本質(zhì),若要真正去把握領(lǐng)會它時,卻反面不見其蹤跡。這就是王維詩歌的沖淡美:極淡雅的情感,極平和的心靜,極自然的思慮。
然而這種“淡”,并非淡而無味,而是淡而濃,淡而遠(yuǎn)。既是藝術(shù)純熟的表現(xiàn),又是千錘百煉的結(jié)果。詩的形象近在眼前,真實可感,而詩境全在言外,余味無窮,不至于意盡句中。
【關(guān)鍵詞】王維;道教;竹;云;清靜無為
一、序言
王維是盛唐著名的山水詩人,在唐代享有盛名。他與李白、杜甫一起,據(jù)有三足鼎立之勢。清人徐增在《而庵說唐詩》中指出:“吾于天才得李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diào),子美一代規(guī)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xué)。”又可見王維尚佛,其詩歌受禪宗影響,禪趣盎然。但同時,王維也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在詩歌中也有體現(xiàn)。王維早年有一段時間頗傾心道教,到后來也一直沒有割斷這一情緣。他寫過一些神仙詩以及和道士交往的詩。如《魚山神女祠歌》、《桃源行》、《贈焦道士》、《贈東岳焦煉師》、《過太乙觀賈生房》、《送方尊師歸嵩山》、《和尹諫議史館山池》、《贈李頎》、《李居士山居》、《送高道弟耽歸臨淮作》、《送張道士歸山》等詩歌,都跟道家關(guān)系密切。
本文從意象選擇和色彩運(yùn)用這兩個方面著手,通過竹意象和云意象的分析,以及王維在詩歌中經(jīng)常運(yùn)用的青白二色的分析,理解王維與道家的緊密聯(lián)系和其詩歌中蘊(yùn)含的道家清靜無為思想。
二、王維詩歌中的道家思想
王維寫過一些神仙詩。如他在早年出官山東時,作《魚山神女祠歌》。這座神女祠祭祀的是著名的天上玉女智瓊,她和弦超的傳說是六朝以來文人們所艷稱的人、神戀愛故事。王維的這首詩歌中的“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fù)苦”,表現(xiàn)了其傾心神秘的心態(tài)。還有如他的《桃源行》: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坐看紅樹不知遠(yuǎn),行盡青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云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云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里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云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xiāng)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jīng)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變。當(dāng)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云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i
這篇作品是演化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而來。這首詩改變了原作的情節(jié),把在桃花源中避難的人們說成是仙,而陶潛筆下的桃花源也被王維描繪成仙境了。可見王維對道教神仙是向往的,他把自己的社會和人生理想寄托在道家的神仙世界中。
在王維的詩歌中,人們都注意到王維崇信佛教,其實與此同時,王維還和道教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受道教思想的影響很深。他在《過太乙觀賈生房》詩中稱:“謬以道門子,征為驂御臣。”他以道門之子自命,和出家當(dāng)了道士的賈生在早年有過長期的交往。在與道士的交往中,王維還寫了不少贈別詩,如《贈焦道士》、《贈東岳焦煉師》等。在《贈焦道士》詩中寫到:“海上游三島,淮南預(yù)八公。坐知千里外,跳向一壺中。縮地朝朱闕,行天使玉童”,在詩歌中描寫了在天地間悠游自在,不受束縛的神仙形象,表露了心中的無限欽羨之情。王維在學(xué)佛的同時也學(xué)道,《春日上方即事》中提到:“好讀高僧傳,時看辟谷方。”王維詩作中,還經(jīng)常運(yùn)用到道家的典故,如《黎拾遺昕裴秀才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有如下兩句:“白法調(diào)狂象,玄言問老龍。何人顧蓬徑,空愧求羊蹤。”這里的“玄言問老龍”用的就是道家的典故。“玄言問老龍”,出自《莊子?知北游》中的寓言故事:“荷甘與神農(nóng)同學(xué)于老龍吉”,老龍吉作為體悟道性的真人形象出現(xiàn)在其詩歌中,可見王維與道教也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1、意象的選擇
王維在詩歌意象的選擇上,也很受道家的影響,如竹、云等意象。竹代表仙風(fēng)道骨、高潔正直,在道教的仙話傳說中經(jīng)常提到。在很多仙話中,得道成仙之人飛升后就會留下一青竹杖。青竹功用豐富,“青竹不僅是神仙自度的仙化意象,也是神仙度化他人的工具”。ii道教對竹也的確獨(dú)有情鐘,陳寅恪先生說:“天師道對于竹之為物,極稱賞其功用。”道教鐘情于竹是著眼于其“繼嗣”和“壽考”等功能,陳寅恪引《真誥》云:“我按九合內(nèi)志文曰:竹者為北機(jī)上精,受氣于玄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nèi)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jié)繁眾多矣。公試可種竹于內(nèi)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爾乃天感機(jī)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壽考。微著之興,常守利貞。此玄人之秘規(guī),行之者甚驗。”iii而這與神仙長生不死的意蘊(yùn)是一脈相承的。同時竹可以用來比喻人的品格和形象,在《詩經(jīng)》中如《衛(wèi)風(fēng)?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清人陳奐《毛詩傳疏》釋曰:“以綠竹之美盛,喻武公之質(zhì)德盛。”但竹與清高隱逸形象聯(lián)系起來是在魏晉時期。魏晉有不少與竹相關(guān)聯(lián)的隱逸故事,如阮籍、嵇康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iv
一、熱衷功名,感時思報國的豪情壯志――譜寫人與社會和諧的盛世贊歌
和諧社會的目標(biāo)和任務(wù)的提出,不僅符合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趨勢,而且是對我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中精華的繼承和發(fā)揚(yáng),其中關(guān)于“和諧”的思想十分豐富。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兩個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倫和諧;二是天人協(xié)調(diào)。人倫和諧是說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間的關(guān)系;天人協(xié)調(diào)是說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關(guān)系。盛唐士人開闊的胸懷和恢宏的氣度影響到盛唐文學(xué)的風(fēng)貌,盛唐詩人的作品中往往表現(xiàn)出熱衷功名、感時思報國的豪情壯志,譜寫出一曲曲人與社會和諧的盛世贊歌,呈現(xiàn)出盛唐詩有的氣象。王維作為這一時期的詩歌作家,與當(dāng)時許多想建功立業(yè)以揚(yáng)名不朽的名士一樣,其早年對功名也充滿熱情、期待與向往,有一種積極進(jìn)取的生活態(tài)度。王維早期仕途比較平坦,他這一時期的詩歌秉承盛唐詩歌的一般主題,多表現(xiàn)對游俠生活的向往和對建功立業(yè)的強(qiáng)烈渴望。他在詩《送張判官赴河西》中說:“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云。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氣魄宏大,洋溢著壯大明朗的情思和氣勢。其奉命赴邊疆慰問將士途中所作的一首紀(jì)行詩《使至塞上》云: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
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蕭關(guān)逢候騎,都護(hù)在燕然。
這首詩以英姿豪逸之氣融貫于出色的景物描寫中,形成雄渾壯闊的詩境。那無盡的長河,廣闊的地平線上的落日,大漠孤堡的烽煙,透露出詩人走馬西來的豪邁氣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兩句,不僅深得塞外風(fēng)光的精髓,而且包藏的胸襟、氣度更不是盛唐以外的文字所能道出的,可見詩人的心境和思想是積極的。
另外,王維的《老將行》《燕支行》這兩首詩描寫邊塞戰(zhàn)爭的宏偉場面,歌頌將士浴血疆場,以身報國的雄心壯志與颯爽英姿,表現(xiàn)了王維對理想社會的向往與追求,從另一個側(cè)面表現(xiàn)了典型的盛唐精神。其慷慨、豪放、激情、浪漫共同匯聚為青春的歌唱,而對人與社會和諧的追求、對國家的獻(xiàn)身精神和對未來的向往使這種歌唱具有堅實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和精神價值,透露開朗、開放的自由精神。在這些詩中透視著王維對當(dāng)時的社會沒有過多的指責(zé),多半持肯定的態(tài)度,我認(rèn)為這些主要源于當(dāng)時國力強(qiáng)盛,為王維等人士提供了實現(xiàn)儒家所倡導(dǎo)的“濟(jì)蒼生,安社稷”、“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的條件和可能。儒家所倡導(dǎo)的政治理論想用生態(tài)美學(xué)的理論推之,無疑是人與社會和諧的體現(xiàn)。即人與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也是其詩呈現(xiàn)出的生態(tài)美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寄情山水,“佛眼”觀萬物――人與自身和諧的注解,人與自然和諧的詮釋
王維的詩風(fēng)在40歲(公元741年左右)前后發(fā)生了變化,由前期的積極關(guān)注現(xiàn)實轉(zhuǎn)變?yōu)閷ι剿飯@的歌唱和對禪境的體悟和沉思。他的詩風(fēng)轉(zhuǎn)變的原因,一方面是王維耳濡目染佛家的東西,這對他早年的思想無疑是有影響的,另一方面是后期仕途的艱難和不平,加之安史之亂后唐朝社會矛盾層出不窮,使其早年的進(jìn)取之心日衰而退隱之心漸生。
王維很早就歸心于佛法,精研佛理,受當(dāng)時流行的北禪宗的影響較大。他在詩《秋夜獨(dú)坐》中說“欲知除老病,惟有學(xué)無生”。學(xué)生的具體方法是坐禪,即靜坐澄心,以最大限度地平靜思想和情緒,讓心體處于近于寂滅的虛空狀態(tài),這能使個人內(nèi)心的純粹意識轉(zhuǎn)化為直覺狀態(tài),如光明自發(fā)一般,產(chǎn)生萬物一體的洞見慧識和渾然感受,進(jìn)入“物我冥合”的無我之境。這種以禪入定,由定生慧的精神境界,對王維山水詩的創(chuàng)作影響極大。禪境通過詩境表現(xiàn),如王維《終南別業(yè)》:“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水的盡頭,自然是深山空靜無人處,人無意而至此,云無心而出,可謂思與境,神會于物。詩人著重寫無心,寫偶然,寫坐看時無思無的直覺印象,那無心淡泊,自然閑適的云是詩人心態(tài)的形象寫照。仕途坎坷的王維處在世俗煩擾的當(dāng)時對他來說是比較可行的方法,這給生態(tài)美學(xué)提出的人與自身的動態(tài)平衡作了一個不錯的注解。
王維的詩,尤其是田園山水詩所呈現(xiàn)出的生態(tài)美思想,對人與自然的和諧能作出比之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身的和諧更重要的詮釋。受佛教影響頗深的王維,有“詩佛”的美譽(yù)。“天下名山僧占多”,光從這點(diǎn)就可以看出佛與山水自然的密切聯(lián)系。有生態(tài)美學(xué)家認(rèn)為只有把自然當(dāng)做與自己一樣的主體,而不是當(dāng)做異己的客體和索取的對象,才能通過交流、體驗而建立自由、和諧的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王維在佛教的影響下,可以說是以一個佛教禪師的身份,以一個佛教信徒“普度眾生”的胸襟,以一雙“佛眼”審視萬物,視天下蒼生與己平等,用心破解萬物的語言密碼,并與之進(jìn)行坦誠、深入的交流。王維與自然萬物的融洽相處,用心交流在其田園山水詩中有很好的詮釋。如其詩《山居秋瞑》:
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息,王孫自可留。
[唐]王 維
渭城朝雨徘岢荊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
詩詞故事
桃t柳綠的春天,在長安西郊的一家小酒館內(nèi),王維和元二在臨窗的方桌前相對而坐。
早晨一場霏霏細(xì)雨,壓住了道路上的灰塵。被雨水沖洗過的柳樹碧綠如新,映襯得驛站屋舍也透出青青的顏色。這場雨洗凈了道路的塵土,卻恰到好處地沒有造成泥濘,仿佛特意為即將出行的旅人安排好了路途。
窗外的柳條兒被輕風(fēng)吹進(jìn)了窗內(nèi),拂在王維和元二的頭上,兩人不約而同地輕輕皺起眉頭,陷入了回憶:一起作詩繪畫,一起撫琴高歌,一起遠(yuǎn)足踏青……而此刻,兩人即將分別。
元二帶著朝廷的任命出使安西,那里距離首都有萬里之遙。出了陽關(guān)就是大片的荒涼土地,旅途艱辛。元二輕嘆:“多少人向往著去西域建功立業(yè),我也不例外,但是這一路的艱難和寂寞,又有誰知道呢?事情是否順利,什么時候能夠完成,又有誰能說得清呢?”王維安慰好友:“這一去雖然辛苦,但是你肩負(fù)著朝廷的重任,必將成就一番壯舉。”兩人回憶著失意時候的相互陪伴,落寞時候的相互照顧,滿腔的不舍化為一杯又一杯醇酒。
離別的時刻到來了。王維仿佛下定決心似的,毅然站起來,舉起酒杯對好朋友說:“來,再喝一杯酒就出發(fā)吧,出了陽關(guān),就再也見不到老朋友了。”元二強(qiáng)忍淚水,與王維干杯道別。
渭城的柳樹年年綠,多少西去的旅人在這里與親友道別。王維譜寫的《渭城曲》,成了他們最常想起的道別詞:“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
(彭營中心小學(xué)天使班 韓雅崢)
寫作啟示
我們知道,王維的作品被評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這首詩的前兩句,給我們呈現(xiàn)出來的畫面多么美好――清朗的天宇,潔凈的道路,青青的客舍,翠綠的楊柳,構(gòu)成了一幅色調(diào)清新明朗的圖景。為這場送別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環(huán)境。這是一場深情的離別,卻透露出一種輕快而富于希望的情調(diào)。
【關(guān)鍵詞】作品;語言風(fēng)格
一、語言風(fēng)格的定義
既然語言風(fēng)格對文學(xué)作者和作品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那么什么才是語言風(fēng)格呢?語言風(fēng)格是指語言風(fēng)格學(xué)的核心術(shù)語,是語言風(fēng)格理論研究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關(guān)于什么是語言風(fēng)格,學(xué)術(shù)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一般來說,“語言風(fēng)格是人們運(yùn)用語言表達(dá)手段形成的諸特點(diǎn)的綜合表現(xiàn),它包括語言的民族風(fēng)格、時代風(fēng)格、流派風(fēng)格、個人風(fēng)格、語體風(fēng)格和表現(xiàn)風(fēng)格”,它“是在主客觀因素制導(dǎo)下運(yùn)用語言表達(dá)手段的諸特點(diǎn)綜合表現(xiàn)出來的格調(diào)與氣氛。”
二、作品語言風(fēng)格的形成
不同的作品,不同的作家都有自己獨(dú)特的語言風(fēng)格,哪么一個作家或者一個作品的語言風(fēng)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一)作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決定了作品的語言風(fēng)格
作品的語言風(fēng)格說到底就是作者的語言風(fēng)格,作家的語言風(fēng)格直接反映到了作品中去了。所謂個性就是個別性、個人性,就是一個人在思想、性格、品質(zhì)、意志、情感、態(tài)度等方面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質(zhì),這個特質(zhì)表現(xiàn)于外就是他的言語方式、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等等,任何人都是有個性的,也只能是一種個性化的存在,個性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個性是作家
獨(dú)特的生活經(jīng)歷、實踐經(jīng)驗、思想觀點(diǎn)、性格氣質(zhì)、知識修養(yǎng)和藝術(shù)才能的結(jié)晶。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和思想感情,因此,作家不同的創(chuàng)作個性,就決定了他們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會選擇不同的詞匯,運(yùn)用不同的表達(dá)方式,從而使其文學(xué)作品的語言呈現(xiàn)不同的氣勢,體現(xiàn)不同的風(fēng)格,也就流露出不同的情感和思想,進(jìn)而寫出不同語言風(fēng)格的文學(xué)作品。如蘇軾的詞,蘇軾性格豪放大氣,寫的詞也大都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蘇軾的詞主要是豪放的風(fēng)格與他的個性是緊密相連的。這種豁達(dá)、開朗的個性注定了蘇軾的詞大都是豪氣沖天、充沛激昂的詞。如在《江城子 密州出獵》中將蘇軾的豪邁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老夫聊發(fā)少年狂”顯示出作者的豪邁氣概,“親射虎,看孫郎”表明作者要像孫權(quán)一樣射殺猛虎,其言豪壯,狂態(tài)可掬。與蘇軾相反地是婉約派的李清照。李清照是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其詞主要是哀婉細(xì)膩,富有傷感,這也比較符合李清照委婉細(xì)膩的個性特征。李清照在前期處境優(yōu)越、夫妻相得,但到了晚年受到國破家亡之變和喪夫之痛,作品變得哀婉凄苦,富有傷感,變的觸景傷情,哀婉細(xì)膩。如在李清照的《聲聲慢》中“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短短的幾句話就把詞人一個人獨(dú)守空房,思念丈夫的哀婉傷感的感情表露出來了。因此,不同作品的有著不同的語言風(fēng)格很大程度上是其作者不同個性造成的,作者個性在語言風(fēng)格形成中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
(二)作品的語言風(fēng)格形成還受到時代特征的影響
每個作品都產(chǎn)生在特定的時代,不同的時代都有其獨(dú)特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環(huán)境,一切社會生活都不可能超越時代,作者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也是時代社會的一個方面。其創(chuàng)作作品的語言風(fēng)格也必然受時代風(fēng)格的影響,因此特定的時代給作品的語言風(fēng)格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杜甫和王維的作品就是兩種語言風(fēng)格的作品。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zhuǎn)衰的時代,戰(zhàn)爭頻繁,百姓困苦不堪,其中“三吏”“三別”(《新安吏》《石壕吏》《潼關(guān)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表現(xiàn)的尤為明顯,真實地描寫了特定環(huán)境下的縣吏、關(guān)吏、老婦、老翁、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語言,生動地反映了安史之亂時期的社會現(xiàn)實和廣大勞動人民深重的災(zāi)難和痛苦,這種時代特點(diǎn)使杜甫的作品的語言風(fēng)格呈現(xiàn)悲傷、憤慨和沉郁的特點(diǎn)。而與杜甫相反的是王維的作品的語言風(fēng)格就與杜甫的截然不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杜甫和王維生活時代的不同,與杜甫生活在唐朝衰落的時代不同的是王維生活在盛唐,政治清明,經(jīng)濟(jì)繁榮,百姓安居樂業(yè),這種時代背景下,王維寫的作品的語言風(fēng)格主要呈現(xiàn)清新、自然地特點(diǎn),多是描寫田園和自然風(fēng)光。因此,作品語言風(fēng)格的形成還受時代特征的影響,不同的時代造就了不同的語言風(fēng)格。
總結(jié):
作品語言風(fēng)格是區(qū)別不同作品類型的一個重要特征,不同的作家會寫出不同語言風(fēng)格的作品,而其語言風(fēng)格的形成受到作者個性和時代特征的影響。
參考文獻(xiàn):
關(guān)鍵詞: 王維 山水田園詩 “詩中有樂” 聲音藝術(shù)
蘇軾說:“味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的確,王維的山水田園詩融畫于詩中,字里行間似用水墨鋪陳出青綠山林,使人如臨其境。值得注意的是,王維的作品不僅詩中有畫,而且詩中有樂——有山有水有清音,可謂“有聲有色”。他用筆墨絕妙地捕捉了聲音的精魂,創(chuàng)作出別有洞天的純自然的音樂,這種音樂不僅美在聲律,而且美在內(nèi)容。本文主要討論的就是在格律之外,王詩內(nèi)容的音樂之韻。
一、樂的標(biāo)準(zhǔn):“美”
本文對“音樂”這一概念的界定是:“美好的聲音”,或者說“噪音的對立面”。聲音很難被清晰劃分,這只是一個較模糊的、不能稱之為“定義”的界定,但是這一界定或許并無偏頗之處。無論喜怒哀樂,無論長短,無論風(fēng)格,無論人聲或自然,帶給人美的享受的聲音,皆可稱為音樂。當(dāng)然,“美”的具體判斷標(biāo)準(zhǔn)會因人而異,對“美”的認(rèn)識是見仁見智的事情,關(guān)于“美”的標(biāo)準(zhǔn)的討論也從未停止,但關(guān)于“美”的觀念并非不能統(tǒng)一(只是這“統(tǒng)一”容易流于寬泛,而“美”本就不是可以嚴(yán)格定義的東西),真正的美是毋庸置疑的,是有力量的,是有無窮感染力和魅力的。回到王維的詩上來,雖然讀者沒有“美是什么”的統(tǒng)一答案,但是都不會否認(rèn)詩中流淌出的音樂之美。聲音使得整首詩渾然天成,就像音符使得樂曲完整、流暢、和諧。因此,本文把王維山水田園詩中描繪的大部分聲音歸入音樂的范疇。
二、樂的內(nèi)容:自然之聲與人造之音
聲律一般分成韻腳,旋律(節(jié)拍)和聲調(diào)(高低徐疾)。①那么,聲音的內(nèi)容可以作何種分類?下文嘗試按聲音的源頭,將其分為“自然之聲”和“人造之音”兩類來分析。
自然當(dāng)然是山水田園詩的主角,王詩中對聲音的描繪也集中在自然之音。王維描摹最多的是鳥鳴,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送梓州李使君》),遍山的杜鵑凄鳴渲染了憂傷的氣氛;又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積雨輞川莊作》),黃鸝輕快的鳴囀似乎在為輞川莊的雨過天晴歡欣;再如“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寒食汜上作》),暮春時分的鳥鳴給渡過汜水的詩人平添了幾分寂寥與黯然。鳥鳴似乎是山水田園里亙古不變的背景音樂。除了鳥鳴,還有風(fēng)聲,雨落聲,水流聲,蟬鳴聲,樹葉的沙沙聲……這些都是山水田園必不可少的標(biāo)志性聲音元素。如“倚杖柴門外,臨風(fēng)聽暮蟬”(《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寒蟬本象征愁緒傷情,這里卻“一反常態(tài)”沒有了傷感的色彩,成為了摯友相聚時一段悅耳的配樂;又如“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過香積寺》),在峻峭山中流淌的泉水似在幽咽一般,一個“咽”字準(zhǔn)確描摹了泉水阻塞緩流的聲音和情態(tài)。
王詩中除了有純粹的自然之聲,還有人聲或者絲竹之音。據(jù)《舊唐書·王維傳》記載:“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一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史書記載王維曾擔(dān)任太樂丞,精通音律的他具有深厚的音樂功底和很高的音樂造詣。平日里他琴吹簫,如“松風(fēng)吹解帶,山月照彈琴”(《酬張少府》),在松風(fēng)里對月彈琴,頗有樂趣;“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欹湖》),簫聲里盡是對友人的依依惜別情;“獨(dú)坐幽篁里,彈琴復(fù)長嘯”(《竹里館》),抒盡心中逸氣。除了樂器演奏的聲音,還有深山傳來的低沉鐘聲:“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過香積寺》),還有興之所至的歌唱:“復(fù)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還有人們的日常交談:“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終南山》);還有遠(yuǎn)處傳來的人聲:“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鹿柴》)。王維對人造之音的描摹在山水田園之外的題材中出現(xiàn)得較多些:如“秋槐葉落空宮里,凝碧池頭奏管弦”(《凝碧池》),“健兒擊鼓吹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涼州賽神》),等等。
三、樂的寫法:點(diǎn)到即止與有無相生
說到王維的聲音藝術(shù),點(diǎn)到即止是其特點(diǎn)之一。和《李憑箜篌引》、《琵琶行》那樣直接描寫和鋪陳聲音的篇章不同,在描寫聲音的時候,王維大多是不寫其聲,只寫其動作或情態(tài);或者說,王維并未對聲音進(jìn)行詳細(xì)的鋪展與描繪,只是含蓄和干凈地點(diǎn)到即止,停留在敘述這一層次上。不管是“山月照彈琴”(《酬張少府》),還是“吹簫凌極浦”(《輞川集·欹湖》);不管是“秋水日潺湲”(《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還是“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不管是“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山居秋暝》),還是“獨(dú)坐幽篁里,彈琴復(fù)長嘯”(《輞川集·竹里館》),這些聲音都需要想象來還原,屬于間接描寫,王維僅僅點(diǎn)到即止,是讀者完成了整個音樂的創(chuàng)作過程。這一過程并不難,相反非常自然。由于王維畫意渲染和氛圍營造都極其成功,讀者猶如被帶入王維時空的幽靜山林,在這一超然物外的世界里,鳥鳴、風(fēng)聲、水聲、絲竹之聲都“各得其所”,只等人們來體會;在這一時空里,所有的音樂都已在心中。
這種點(diǎn)到即止的間接描寫典型是風(fēng)聲。比如“松風(fēng)吹解帶”(《酬張少府》),只是描摹風(fēng)吹的動態(tài),然而隱藏的音符——風(fēng)聲仿佛就在耳邊;又如“隔牖風(fēng)驚竹”(《冬晚對雪一壺居士家》),并未直說風(fēng)聲如何,但風(fēng)穿梭在竹林間的聲音和竹林搖曳的沙沙聲依舊撲面而來;再如“人閑桂花落”(《鳥鳴澗》),花落無聲,但卻似乎可以隱約聽到相伴的風(fēng)聲,如此輕緩柔和。這些詩句沒有直接描摹聲音,含蓄中別具韻味和詩意。
〔關(guān)鍵詞〕元代 文人畫 興盛
文人畫,也稱為“士大夫畫”,是指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士大夫所作的畫,多取材于山水、花鳥、梅蘭竹菊和木石等。畫中帶有畫者的情感流露,是畫者真性情在畫中的體現(xiàn)。人們認(rèn)為,唐代的王維是其創(chuàng)始者,并稱為文人畫的鼻祖;把文人畫作為一個具體的概念呈現(xiàn),則是元代趙孟\提出來的。
一、元代之前的文人畫歷史
早期歷史上,雖然沒有文人之說,但在一些文人、畫家論述繪畫的語言中,已表達(dá)出文人畫的內(nèi)涵與因素。如南北朝宗炳認(rèn)為繪畫能“澄懷觀道,臥以游之。”體現(xiàn)了畫家的自娛心態(tài)。姚最在《續(xù)古畫品》中記蕭賁的繪畫是“不學(xué)為人,自娛而已。”確立了文人畫的中心論調(diào)。
說到文人畫,我們就要提到王維,唐代詩歌盛行,大詩人王維以詩入畫,王維是中國文人畫史上的一個關(guān)鍵人物,被譽(yù)為文人畫之祖、唐代的“詩佛”。 在中國繪畫史上曾出現(xiàn)過一種別具風(fēng)格的畫種,它高遠(yuǎn)淡泊,超然灑脫,滲透著禪的意境,這就是“禪畫”。禪畫筆簡意足,參禪的“詩佛”王維使禪心與畫意融合在其“水墨渲淡”山水畫中,很受當(dāng)時奉佛的文士和佛門中人贊賞,仿效者甚多,于是“禪畫”就形成了。王維首開禪畫先河之后,影響了一批像貫休、石恪這樣的禪畫大家。到了宋代,禪畫達(dá)到了一定的境界;所謂的文人畫,實際上是以禪宗思想為審美原則,追求淡泊高遠(yuǎn)、以意境相尚的禪宗畫;而禪宗畫又把文人畫的簡淡清幽在禪悟中推到了極至。因此,禪畫與文人畫有著極其緊密的淵源聯(lián)系。所以我們可以認(rèn)為,王維是文人畫的始祖,是文人畫的開創(chuàng)者。
雖然后人董其昌把王維尊為文人畫之祖,但名副其實的文人畫形成于元代。因為元代之前有影響的畫家大都入仕,故稱“仕畫”。仕人畫與文人畫是一脈相承的,實際上仕人畫就是后來的文人畫。大都認(rèn)為宋代坡對文人畫的形成與發(fā)展起到關(guān)鍵作用。
坡既是文人畫的倡導(dǎo)者,又是一個著名的文人畫家。他在文學(xué)和書法上有著卓越的成就,作畫只是讀書吟詩之余的事,但對文人畫的發(fā)展卻有很大的影響。他最大的貢獻(xiàn),就是奠定了文人畫的理論基礎(chǔ)。他強(qiáng)調(diào)作品的天然意趣,緣物寄情有感而發(fā);反對論畫止于形似,注重意象造型;提倡詩畫一律,托物言志;表現(xiàn)方法不受程式束縛,強(qiáng)調(diào)畫外意境。蘇軾的理論對后世影響很大,自宋以后,文人畫成為一種潮流,經(jīng)久不衰。
二、元代政治動態(tài)分析
元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長河中一個相對復(fù)雜的朝代,蒙古族入侵中原并掌握朝政,使得不同民族之間、不同宗教之間、不同文化之間產(chǎn)生了矛盾沖突,以及其它諸多不和諧的因素,而這些都對元代文人畫的興盛起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元代的這種自由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首先,元代蒙古統(tǒng)治者是游牧民族,經(jīng)濟(jì)落后,所以他們要用武力征服世界,靠掠奪獲得財富。在元代知識分子得不到重用,甚至是冷落對象。其次,元代統(tǒng)治者對文化缺乏關(guān)心和熱忱,對于繪畫藝術(shù)更是采取漠視的態(tài)度,如廢除科舉制度和廢除畫院,中國歷史幾千年的科舉制度廢除,使得文人士大夫們沒有了仕途上的希冀,無力反抗現(xiàn)狀只能把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通過詩畫表達(dá)出來,而隱逸在當(dāng)時更是成為了逃避現(xiàn)實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再次,蒙古統(tǒng)治者對漢民族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將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身份依次分等級,漢人特別是文人士大夫在元代失去了在之前歷史上的尊貴身份和優(yōu)厚待遇,他們在精神上十分苦悶壓抑和悲涼。
三、元代文人畫興盛原因
文人畫在元代之前并沒有得到大力的推崇,為什么到了元代卻興盛起來了呢?這里面包含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1、新的畫材運(yùn)用。在元代繪畫材料有了變化,主要是指在生宣紙上作畫。元代文人畫家喜歡在生紙上作畫,生紙這種材料正好適合于表達(dá)山水畫的這種“寫”的書法趣味,促使元代山水畫的形式產(chǎn)生了轉(zhuǎn)變,這對元代文人畫的興盛有一定的促進(jìn)作用。
2、元初因畫院的解體,元朝統(tǒng)治者不重視繪畫藝術(shù),與宋代統(tǒng)治者對畫院的控制權(quán)相比,元代畫家都已經(jīng)不再受他人指使,文人畫家們不必去附和他們的審美需要,而可以根據(jù)個人喜好去選材和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上已經(jīng)相對自由,不再作為政治消遣,而當(dāng)作寄情山水、發(fā)泄情感的一種方式,從而形成自己的藝術(shù)風(fēng)格。
3、元代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導(dǎo)致了文人的歸隱,但也因此而促使了他們成為繪畫創(chuàng)作的主體。元代統(tǒng)治者對中原文化淡漠,文人士大夫任自己的畫筆在天地間自由的揮灑,他們對周遭動蕩的社會置若罔聞,而是醉心于自己另一個世界,像他們所仰慕的高人志士一樣,悠閑的賞月、垂釣、對弈、吟唱,如此恬適清閑,形成特有的元代文人的人生信仰和精神取向。他們的作品天真爛漫、放逸灑脫,也使得文人畫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會如此興盛。
4、元代文人畫的杰出代表的推動。元四家是指黃公望、吳鎮(zhèn)、倪瓚、王蒙四位生活在江浙一帶的畫家。他們生活于元末社會動亂之際,雖然每個人的社會地位及境況不同,但都有不得意的遭遇,藝術(shù)上直接或間接地受趙孟\的影響。元四家的作品雖然都有各自的創(chuàng)新風(fēng)格和獨(dú)特的藝術(shù)手法,但是他們都擅長詩書畫印的結(jié)合,都強(qiáng)調(diào)繪畫的娛樂性,注重筆墨趣味。他們的山水畫代表了中國山水畫史上的一個高峰,也是中國文人畫成熟的標(biāo)志。
文人畫家們以非凡的功力成功地將詩的意境、書的筆法、畫的傳統(tǒng)通過對自然景物的感受,默契神會,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元代是文人畫進(jìn)入全面成熟和完善的階段,成為中國文人畫運(yùn)動中最重要的一環(huán),也是文人畫運(yùn)動的里程碑,代表著中國山水畫的發(fā)展方向。 (責(zé)任編輯:劉小紅)
參考文獻(xiàn):
[1]王宏建、袁寶林.美術(shù)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2]黃冬富.中國美術(shù)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